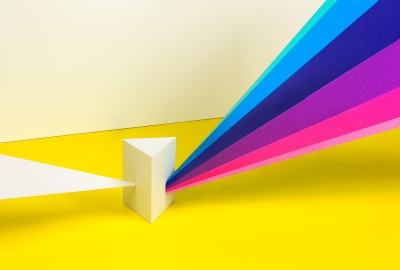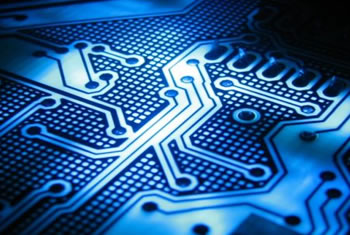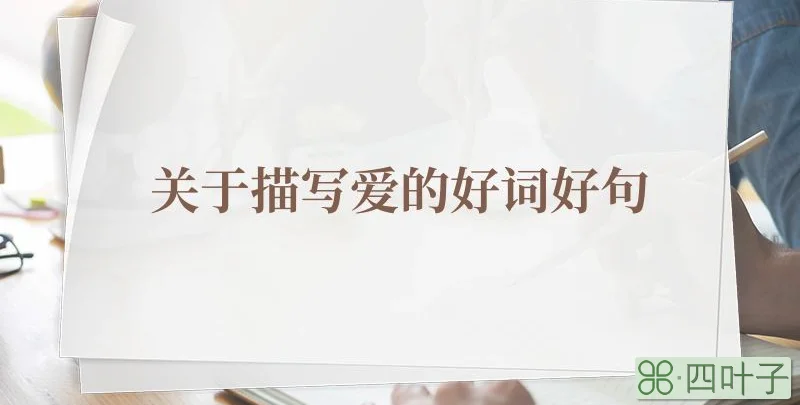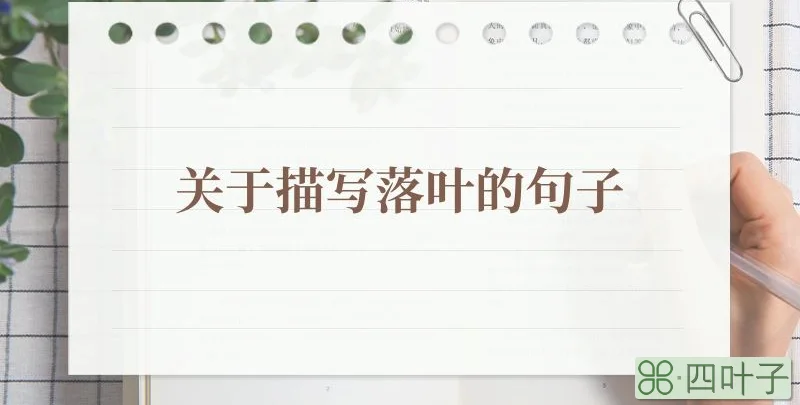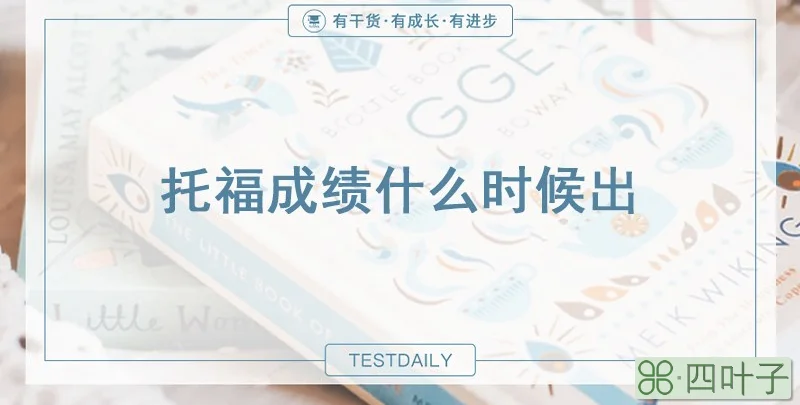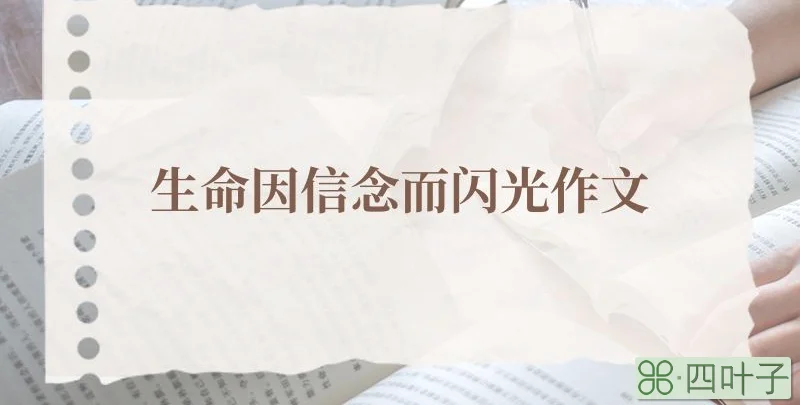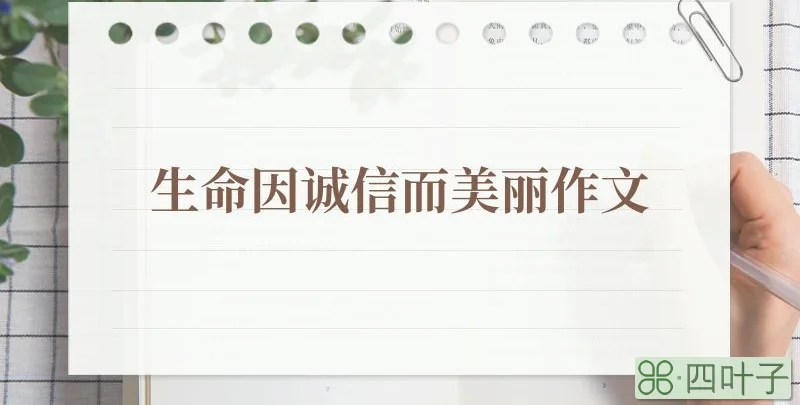树和天空分析

《树和天空》分析:
首先,树在这里被作为生命主体,取得了超越于人的自觉和主动性。虽同处雨中,但是“走动”、“有急事”、“汲取生命”、“停住脚步”和“等待”的却首先是树而不是人。“我们”在这里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见证人、陈述者——一个同路人。而“我”(如果可以这样推测诗人的话)则更是仅仅作为“我们”的一个代言人而已,仅仅是目睹了自然生命律动的一个记录员。(然而这里并不是要走向另一个极端去重树轻人,只是因为自然只以其存在表示自己,而人还有使用文字的能力)树在这里有行动(“走”)、有计划(“有急事”)、有对生命自觉自为的争取与充盈。甚至还有着它的宗教般的静观和对于未来一种唯美的期待。
同时,在树的自由意志里,还融会着宇宙间一种互相谐和与默契的情怀与品质。阳光或者雨露,阴晴还是雨雪,物类间并没有相互冲突的必然理由。因为即便在“灰色”中也依然可以“汲取生命”,而那“园里黑色的山雀”,更是一个关于生命的积极乐观又欢愉的精灵。真正健全的生命懂得享受自然的每一种赐予。于是在“晴朗的夜晚”才有了它们更为“挺拔”的身姿。而支撑这一切的,除了对宇宙规律的默认,更多的应该还是对那个雪花绽开的瞬间最为坚执的等待!“雪花”在这里有着丰富的蕴涵。作为冬天的象征,它不可避免地预示着寒冷,然而“严寒尤有傲霜枝”,它又恰恰提供了强力意志最充分的突显。承续前文,它又是万物对宇宙规律一次充满自信的认可与迎取。如果可以,我还希望它会是人类对生命暂歇的期许。宇宙自有它的动静,自然也有着它四时的更替,而永远忙忙碌碌的人们,是否也应该有一个停下脚步、静观夜空的瞬间?——就像一个农人在辛苦的劳作中也会偶尔抬起头来,欣赏那飘着白云、飞着鸟群的天空,于是知道自己的辛勤并不惘然与孤独。而从审美的维度,“雪花”更象征着一个洁白澄净的纯美境界,一种超越了世俗功利、摆脱了欲望和俗物的牵绊、万物融和无间、和谐共存的圆融化境。在这个世界里,人与物、人与人、物与物,一切存在之间的距离都将泯灭而消失殆尽,只剩下轻轻飘来的一阵宇宙间的清丽气息。
总体来看,这首诗的前后两节有着层次与境界上的相承与递进。前者主动,后者主静。前者充溢着生命的搏击与律动,启示着自然间一种积极向上的活力。而当“雨歇了”,世界便进入一种行动后的安宁、强力后的静谧。那曾因为争取而匆匆走过的躯体,也终于有了夜空下神圣而静穆的“挺拔”闪现。这是只有在“行到水穷处”之后,才会拥有的“坐看云起时”的坦然境地。虽然那“挺拔”的姿势只是一次“闪现”,虽然“等待”的只是一个“瞬间”,但是存在的意义不就是在那无休止的搏动中一次又一次地追逐那一层高过一层的瞬间化境么?!
运动是存在的永恒形式。而这一切是自然界的同时也是人的存在方式。这首诗的独特处,也就在它的视角虽从“树”落脚,却又能反诸人类自身。如从树“匆匆走过我们身旁”,经由相对运动思维,可以看到人类自身的匆匆脚步;又从“和我们一样”的陈述中,透露出人类同样有着的渴望与自然和谐相处、向往宇宙间的至善至美境地的讯息。而这一角度的高妙,还在于它虽经反诸自身后来却并未再郁于自身,而是点到为止,始终以一种更加阔大、高蹈、超越物类的视角在平等而体贴地观照着一切 。你在这里可以看见人与物异质同构的同一颗博大、纯粹而统一的灵魂。这是一种突破了人类中心而转向宇宙中心的视角,它体现着人类更深刻的关怀意识。
最后要回头再来看一眼诗题。“树与天空”,这里同样充满了隐喻。诗人选择“树”作为观照对象,除了事实的触发,恐怕更多的还在于树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包括树丰富的生态和文化蕴含。作为生物,树是立足于大地同时又指向天空的最隆重和充分的表示。它对生命应有的在地下的深度以及永无止境的向上的高度都作了最为坚实而高贵的展览和诠释。于是,树连接了大地与天空,此岸与彼岸,现世与终极——是树,让我们看清了自身的位置和应有的走向。
但是为现实所拘郁和蒙蔽的人类,却在漫长的文明进程中越来越遗忘了这种启示。他们埋头于对土地的耕耘与掘进,却渐渐忽略了头顶上还有着的那片令人震撼和心悸的星空。所以诗人要为树提供一个天空——一个既是用来伸展同时也是用来抚慰的天空。在那里,正散布着有关生命的全部隐喻。比如对未知的渴望,比如对神秘的保留与欣赏,比如行路中的驻足、静观与默想,比如对宇宙一声纯粹而又唯美的惊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