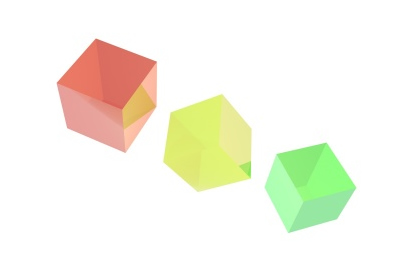城市的精神读后感

因为膝盖受伤和后期恢复的需要,不得不搁置了今年所有的旅行计划。但开阔眼界、调养身心、涤荡精神、学习他人之智慧也并不是只有身临其境才可以。某种意义上讲,读书其实是一种更便捷、更有效的方式。尤其当作者是一位在某个专业领域有建树的领军人时,通过他的视野来解读这个世界,又何乐而不为呢?
《城市的精神》是两位外籍政治哲学家贝淡宁和艾维纳合著的一本深度解读城市精神内核的书。两位作者都是外籍身份的中国大学教授,都有着在世界各地的生活经验和学习经历,作者对书中提及的城市的人文历史和文化特征都有着准确的描述和细致的考察,向读者展现了世界众多大城市及其居民表达出的自身的独特习性和价值观。整卷翻完,受益良多。
书中,作者选取了耶路撒冷、蒙特利尔、新加坡、香港、北京、牛津、柏林、巴黎、纽约共九个城市进行深入解读,这几个城市无一例外的在某一方面有着自身独特的、鲜明的特点,如柏林——宽容、巴黎——浪漫、北京——政治、纽约——抱负。作者对城市的建筑和物质外观着墨很少(点到为止),也没有宏大叙事的行政精神,而是着力体现自治的、自由与自我的自下而上的市民精神,一种真正的城市精神。笔者在感慨作者视野思维宽广深刻的同时,也不禁对以往自己对一些城市的肤浅认知而深感惭愧。
比如巴黎。相信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与其他任何城市相比,巴黎更是一个充满浪漫梦想的城市。只是,我们如何解读“浪漫”,巴黎人又如何解读“浪漫”,两者是否一致?我们对巴黎浪漫的印象或许来自于好莱坞电影中巴黎街头接吻的青年男女、或许来自于巴黎街角的悠闲舒适的咖啡馆、亦或许来自于法国总统的花边新闻。但实际上,受访的巴黎本地人对巴黎的浪漫(好莱坞版本的浪漫)假设充满怀疑甚至敌视。巴黎人的浪漫精神体现在:他们看待日常生活的途径是贬低物质享受,赞美英雄的个人主义,尊重传统而非消费主义,尊重道德而不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思考,将反正统思想的态度理想化,不怎么关心表面的社会地位。在巴黎,讨论金钱或社会地位等话题是令人反感的;卢梭对摆脱社会规范束缚的个人自我的理想化和对现代文明的压迫和不平等的攻击成为19世纪浪漫主义的关键主题;一位在巴黎出生并成长的中国古典政治学者远离巴黎后最想念的是巴黎的思想生活、对话和娱乐;在巴黎,观点变成了理想,任务变成了让现实适应理想,而不是让理想适应现实。
比如柏林。如今的柏林,作为德国的艺术、文化和自由中心的声誉日隆,除了成为文化中心外,柏林一直在进行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迷人工程。这些工程包括建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反犹运动纪念地、把主要大街命名为从前受害者的领导人以及柏林墙的建立等等,让居民和游客了解到包括纳粹时期和东柏林时期在内的城市历史。在对待其他种族与文化的态度上也愈加宽容、透明、开放。与过去和解的意图不是恢复任何形式的关系,而是创造一种正确关系,而创造新关系的前提是牢记过去以避免悲剧再次发生(历史上,柏林在宽容与不宽容之间几经摇摆,宽容政策带来了文化繁荣和富足,不宽容政策对其发展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为二战加害国的日本,歪曲历史、否认历史甚至杜撰历史,近日,安倍甚至以二战后欧洲的大团结氛围才使得德国表现出道歉与和解的态度,而亚洲并没有这种氛围,所以拒绝道歉与和解。笔者认为恰恰相反,正是德国的道歉与反省推动和促进了欧洲的一体化和大团结氛围,日本的不直面历史、不承认历史,不给受伤害的国家和民族一个可以接受的态度,严重阻碍和影响了亚洲的一体化和大团结氛围的形成和构建,安倍之言可谓诡辩。反思与道歉是和解的最基本的前提。
比如纽约。1626年,荷兰人用60荷兰盾(约24美元)的小饰物和其他商品从勒那皮印点人手中买下了曼哈顿岛,大约二、三十年后曼哈顿在国际贸易的刺激下发展成为多民族聚居的大商业城市。1893年,曼哈顿、布朗克斯、斯塔滕岛、昆斯、布鲁克林合起来构成“大纽约市”,城市人口增加了一倍,地里面积从曼哈顿的23平方英里扩展到300平方英里。有人把纽约经济成功的原因归结为地理位置优势,依此逻辑,纽约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应该伴随着港口重要性的下降而下降才对,但真实的情况恰恰相反。那么,纽约作为世界主要经济城市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作者将其归功于外来移民的大规模涌入以及纽约向移民传达的一种欢迎和鼓励的信息。一方面外来移民大多充满了“干大事”的勃勃雄心,为当地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源源不断的能量,“正是多种不同雄心勃勃者的视角冲突是纽约成为世界首都”;另一方面,纽约形成了一种把友谊与尊重隐私结合起来的社会规范,为雄心勃勃者提供了能挥洒自己天赋的活动空间。国内一些城市或地方的领导者和人们或许应该反思,对外来人口的排斥以及对地方的过度保护是否阻碍了本地的发展,为眼前的和个人的利益而放弃了长远的整体的利益?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城市精神的解读,始终是客观的的、全面地、立体的,不仅向读者展示其积极向上的的一面,也向读者描述其矛盾、落后的因素,比如在解读柏林时作者对宽容与冷漠之间界限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