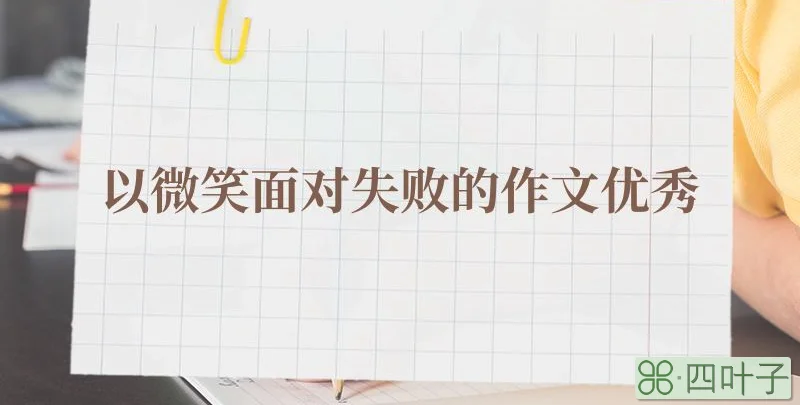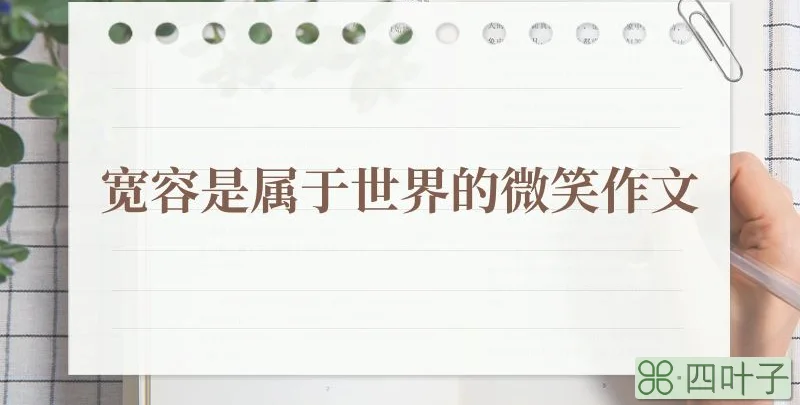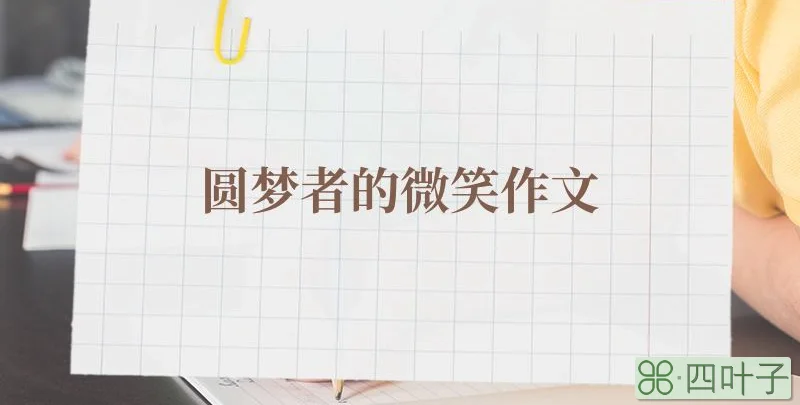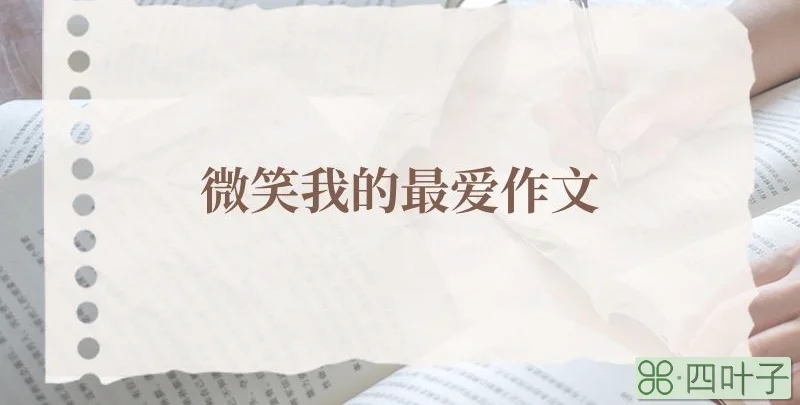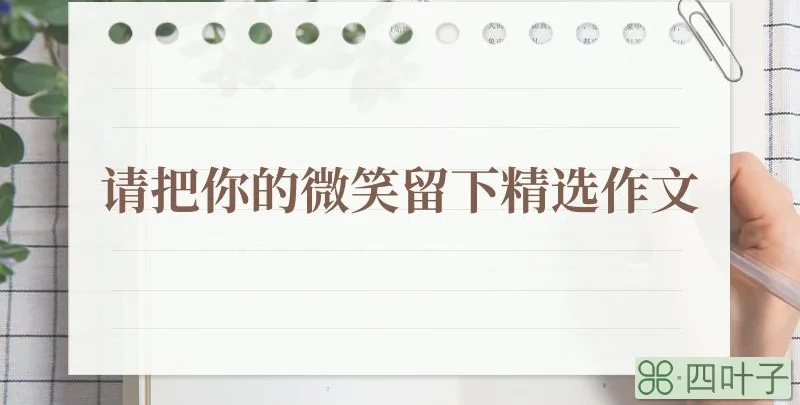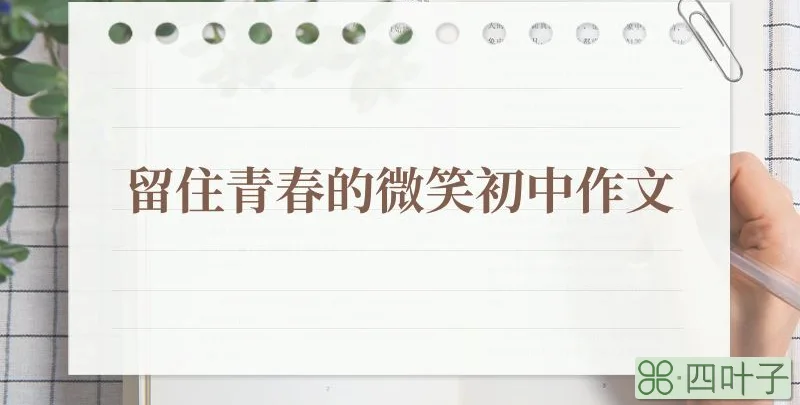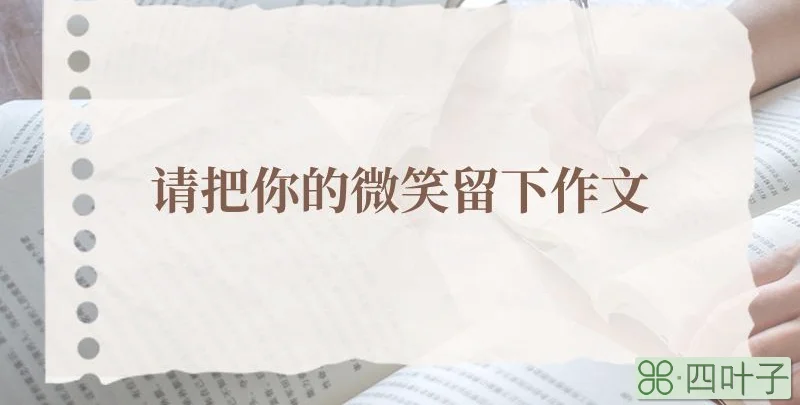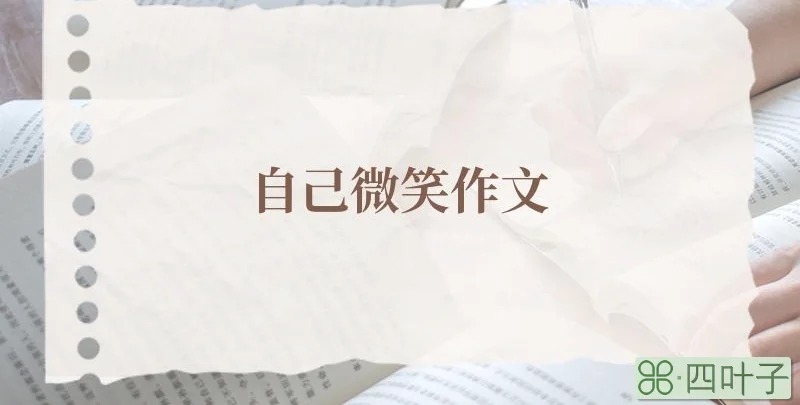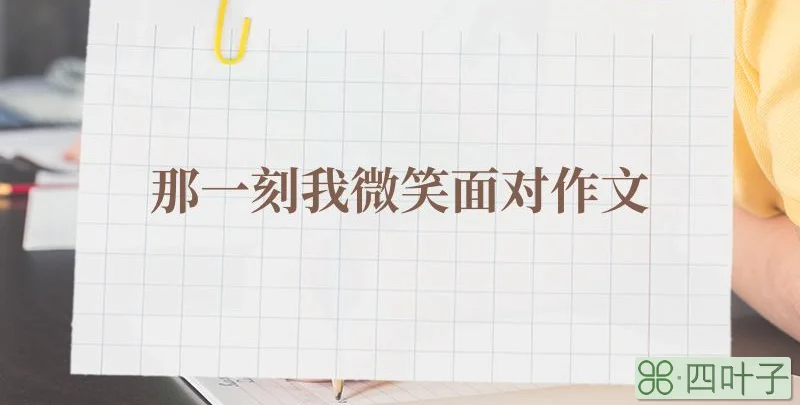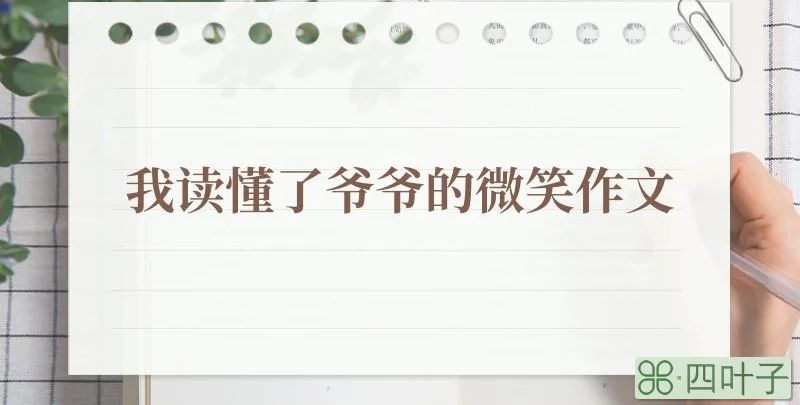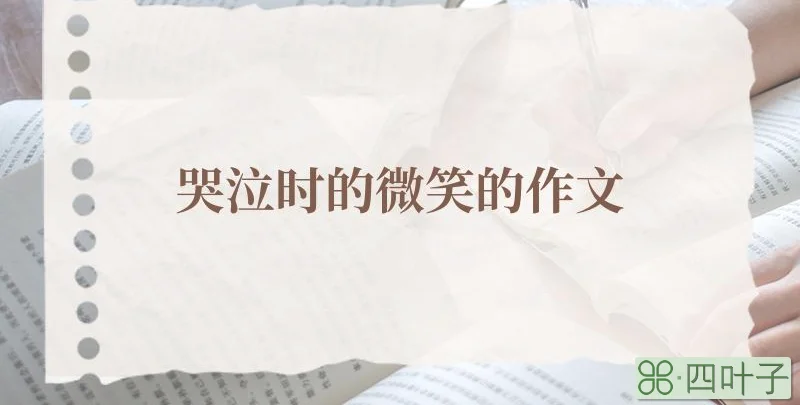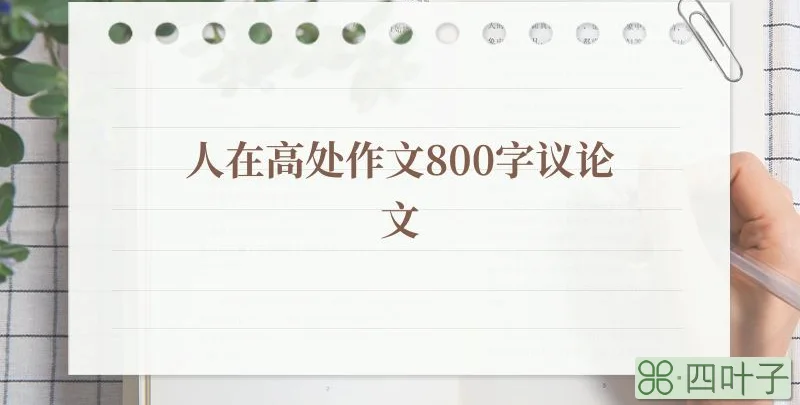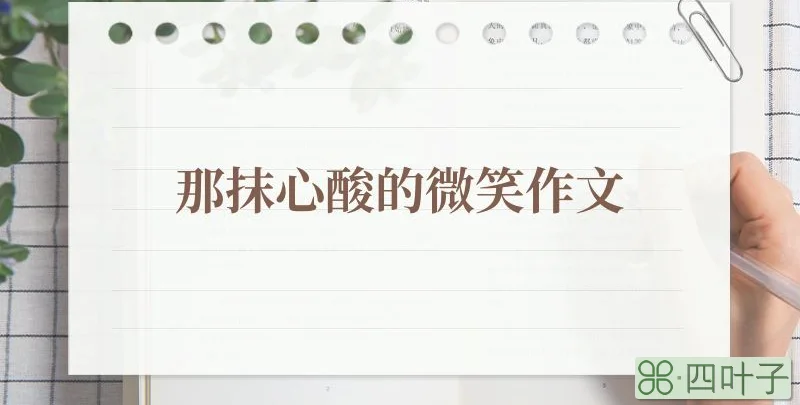白衣天使的微笑作文800字
白刷刷的灯光照在白刷刷的墙上,让人感到冷峻。周围弥漫着一股药水味,搅拌着我的恐惧,在空中发酵。我坐在冰冷的不锈钢椅子上,那椅子像寒剑刺向我,让我坐立不安。
周围的病号像凋谢的花儿,无力地瘫坐在椅子上,好像准备要上刑场一样。护士推着注射车在我面前穿梭,嘎吱嘎吱的碾过,真像冷漠的勾魂索魄的白无常。在我的一惊一乍中,恐惧滋长了。
注射车的声音把晕晕沉沉的我唤醒了,护士正向我走来。睁开沉重眼皮,朦胧中,我并没有看清她的容颜。心想:又是哪个倒霉鬼准备扎针了?在我的惶惑中,她走到我的面前:“你是小A吗?”她那声音轻轻拂过,掀起了一阵涟漪,轻轻地漾进我的耳朵。
还有一种让我感到舒适的东西,我却捕捉不到。这一刻,我终于看到了她的容颜:嘴角上扬,露出迷人的梨涡浅笑,把我要打针的阴霾给散去了。我宽下心来,护士也不是凶神恶煞的嘛。
那迷人的笑容足以抵挡医院冷峭带来的恐惧。于是,我强打精神,把手伸出去,接受“用刑”。手是伸出去了,却在不争气地颤抖着。
我在心理哀求:护士姐姐,打轻一点。护士分明读出了我的心里话:“没事,不疼的,就像被蚊子叮一样。”说完,她拿出蘸有碘酒的棉签在我的手臂上轻柔、娴熟地擦。
棉签好像在轻舞,连同包裹我的恐惧也一并擦掉。护士向我妈妈使眼色,示意她摁住我的手臂。我从她的神态看出马上要上“死刑”了。
护士这时和我拉起了家常:“小A,今年几岁了?”“10岁。”“几年级?”……护士那柔和的声音里沾满了关爱,把我的恐惧给熨平了。我的手臂一开始像被蚊虫叮咬,“我的妈呀!痛啊!”一阵刺痛向我袭来,正发作时,护士驾轻就熟地把针打完了。
针虽然打完了,但我依然张皇地配合护士把血止住。护士一边收拾用具,一边绽放出迷人的笑容,还褒奖我:“真棒!你很勇敢!”我听了使劲点了点头回应。护士把注射车推向了另一个病人。
我只能报以感激的目送。这时我觉得医院的灯光也不再那么刺眼,墙也不再那么冰冷。周围嵌着护士那迷人的笑容,她带给我的美好氤氲在我的周围。
一开始令我舒适又捉摸不到的东西,这一刻捕捉到了:护士那柔美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