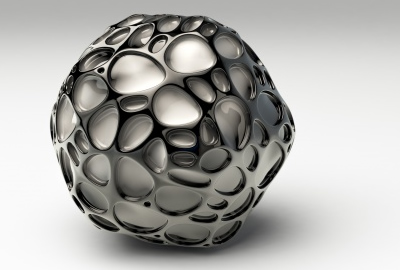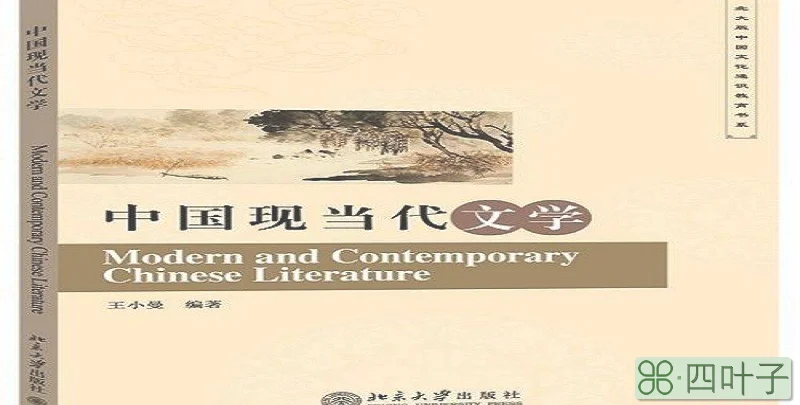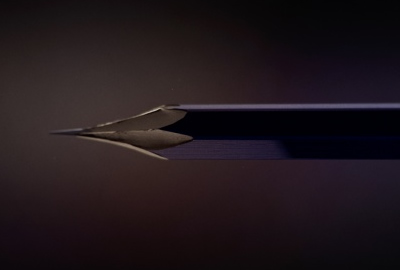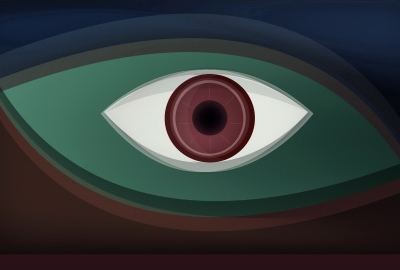文学的趣味讲的意思是啥

文学作品在艺术价值上有高低的分别,鉴别出这高低而特有所好,特有所恶,这就是普通所谓趣味,辨别一种作品的趣味就是评判,玩索一种作品的趣味就是欣赏,把自己在人生自然或艺术中所领略得的趣味表现出就是创造。趣味对于文学的重要于此可知。文学的修养可以说是趣味的修养。趣味是一个比喻,由口舌感觉引申出来的。它是一件极寻常的事,却也是一件极难的事。虽说“天下之口有同嗜”而实际上“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它的难处在没有固定的客观的标准,而同时又不能完全凭主观的抉择。说完全没有客观的标准吧,文章的美丑犹如食品的甜酸,究竟容许公是公非的存在;说完全可以凭客观的标准吧,一般人对于文艺作品的欣赏有许多个别的差异,正如有人嗜甜,有人嗜辣。在文学方面下过一番功夫的人都明白文学上趣味的分别是极微妙的,差之毫厘往往谬以千里。极深厚的修养常在毫厘之差上见出,极艰苦的磨练也常在毫厘之差上做功夫。
举一两个实例来说。南唐中主的《浣溪沙》是许多读者所熟读的:
“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
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何限恨,倚阑干。”
冯正中、王荆公诸人都极赏“细雨梦回”二句,王静安在《人间词话》里却说:“菡萏香销二句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乃古今独赏其细雨梦回二句,故知解正不易得。”《人间词话》又提到秦少游的《踏莎行》,这首词最后两句是“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最为苏东坡所叹赏,王静安也不以为然:“少游词最为凄惋,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而为凄厉矣。东坡赏其后二语,犹为皮相。”
这种优秀的评判正足见趣味的高低。我们玩味文学作品时,随时要评判优劣,表示好恶,就随时要显趣味的高低。冯正中、王荆公、苏东坡诸人对于文学不能说算不得“解人”,他们所指出的好句也确实是好,可是细玩王静安所指出的另外几句,他们的见解确不无可议之处,至少是“郴江绕郴山”二句实在不如“孤馆闭春寒”二句。几句中间的差别微妙到不易分辨的程度,所以容易被人忽略过去。可是它所关却极深广,赏识“郴江绕郴山”的是一种胸襟,赏识“孤馆闭春寒”的另是一种胸襟;同时,在这一两首词中所用的鉴别的眼光可以应用来鉴别一切文艺作品,显出同样的抉择,同样的好恶,所以对于一章一句的欣赏大可见出一个人的一般文学趣味。好比善饮酒者有敏感鉴别一杯酒,就有敏感鉴别一切的酒。趣味其实就是这样的敏感。离开这一点敏感,文艺就无由欣赏,好丑妍媸就变成平等无别。
不仅欣赏,在创作方面我们也需要纯正的趣味。每个作者必须是自己的严正的批评者,他在命意布局遣词造句上都须辨析锱铢,审慎抉择,不肯有一丝一毫的含糊敷衍。他的风格就是他的人格,而造成他的特殊风格的就是他的特殊趣味。一个作家的趣味在他的修改锻炼的功夫上最容易见出。西方名家的稿本多存在博物馆,其中修改的痕迹最足发人深省。中国名家修改的痕迹多随稿本湮没,但在笔记杂著中也偶可见一斑。姑举一例。黄山谷的《冲雪宿新寨》一首七律的五六两句原为“俗学近知回首晚,病身全觉折腰难”。这两句本甚好,所以王荆公在都中听到,就击节赞叹,说“黄某非风尘俗吏”。但是黄山谷自己仍不满意,最后改为“小吏有时须束带,故人颇问不休官。”这两句仍是用陶渊明见督邮的典故,却比原文来得委婉有含蓄,弃彼取此,亦全凭趣味。如果在趣味上不深究,黄山谷既写成原来两句,就大可苟且偷安。
以上谈欣赏和创作,摘句说明,只是为其轻而易举,其实一切文艺上的好恶都可作如是观。你可以特别爱好某一家,某一体,某一时代,某一派别,把其余都看成左道狐禅。文艺上的好恶往往和道德上的好恶同样地强烈深固,一个人可以在趣味异同上区别敌友,党其所同,伐其所异。文学史上许多派别,许多笔墨官司,都是这样起来的。
在这里我们会起疑问:文艺有好坏,爱憎起于好坏,好的就应得一致爱好,坏的就应得一致憎恶,何以文艺的趣味有那么大的纷歧呢?你拥护六朝,他崇拜唐宋;你赞赏苏辛,他推尊温李,纷纭扰攘,莫衷一是。作品的优越不尽可为凭,莎士比亚、布莱克、华兹华斯一般开风气的诗人在当时都不很为人重视。读者的深厚造诣也不尽可为凭,托尔斯泰攻击莎士比亚和歌德,约翰逊看不起弥尔顿,法郎士讥诮荷马和维吉尔。这种趣味的纷歧是极有趣的事实。粗略地分析,造成这事实的有下列几个因素:
第一是资禀性情。文艺趣味的偏向在大体上先天已被决定。最显著的是民族根性。拉丁民族最喜欢明晰,条顿民族最喜欢力量,希伯来民族最喜欢严肃,他们所产生的文艺就各具一种风格,恰好表现他们的国民性。就个人论,据近代心理学的研究,许多类型的差异都可以影响文艺的趣味。比如在想像方面,“造型类”人物要求一切像图像那样一目了然,“涣散类”人物喜欢一切像音乐那样迷离隐约;在性情方面,“硬心类”人物偏袒阳刚,“软心类”人物特好阴柔;在天然倾向方面,“外倾”者喜欢戏剧式的动作,“内倾”者喜欢独语体诗式的默想。这只是就几个荦荦大端来说,每个人在资禀性情方面还有他的特殊个性,这和他的文艺的趣味也密切相关。
其次是身世经历。《世说新语》中谢安有一次问子弟:“《毛诗》何句最佳?”谢玄回答:“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谢安表示异议,说:“訏谟定命,远猷辰告句有雅人深致。”这两人的趣味不同,却恰合两人不同的身份。谢安自己当朝一品,所以特别能欣赏那形容老成谋国的两句;谢玄是翩翩佳公子,所以那流连风景,感物兴怀的句子很合他的口胃。本来文学欣赏,贵能设身处地去体会。如果作品所写的与自己所经历的相近,我们自然更容易了解,更容易起同情。杜工部的诗在这抗战期中读起来,特别亲切有味,也就是这个道理。
第三是传统习尚。法国学者泰纳著《英国文学史》,指出“民族”、“时代”、“周围”为文学的三大决定因素,文艺的趣味也可以说大半受这三种势力形成。各民族、各时代都有它的传统。每个人的“周围”(法文milieu略似英文circle,意谓“圈子”,即常接近的人物,比如说,属于一个派别就是站在那个圈子里)都有它的习尚。在西方,古典派与浪漫派、理想派和写实派;在中国,六朝文与唐宋古文,选体诗、唐诗和宋诗,五代词、北宋词和南宋词,桐城派古文和阳湖派古文,彼此中间都树有很森严的壁垒。投身到某一派旗帜之下的人,就觉得只有那一派是正统,阿其所好,以致目空其余一切。我个人与文艺界朋友的接触,深深地感觉到传统习尚所产生的一些不愉快的经验。我对新文学属望很殷,费尽千言万语也不能说服国学耆宿们,让他们相信新文学也自有一番道理。我也很爱读旧诗文,向新文学作家称道旧诗文的好处,也被他们嗤为顽腐。此外新旧文学家中又各派别之下有派别,京派海派,左派右派,彼此相持不下。我冷眼看得很清楚,每派人都站在一个“圈子”里,那圈子就是他们的“天下”。
一个人在创作和欣赏时所表现的趣味,大半由上述三个因素决定。资禀性情、身世经历和传统习尚,都是很自然地套在一个人身上的,轻易不能摆脱,而且它们的影响有好有坏,也不必完全摆脱。我们应该做的功夫是根据固有的资禀性情而加以磨砺陶冶,扩充身世经历而加以细心的体验,接收多方的传统习尚而求截长取短,融会贯通。这三层功夫就是普通所谓学问修养。纯恃天赋的趣味不足为凭,纯恃环境影响造成的趣味也不足为凭,纯正的可凭的趣味必定是学问修养的结果。
孔子有言:“知之者不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仿佛以为知、好、乐是三层事,一层深一层;其实在文艺方面,第一难关是知,能知就能好,能好就能乐。知、好、乐三种心理活动融为一体,就是欣赏,而欣赏所凭的就是趣味。许多人在文艺趣味上有欠缺,大半由于在知上有欠缺。
有些人根本不知,当然不会盛感到趣味,看到任何好的作品都如蠢牛听琴,不起作用。这是的精神上的残废。犯这种毛病的人失去大部分生命的意味。
有些人知得不正确,于是趣味低劣,缺乏鉴别力,只以需要刺激或麻醉,取恶劣作品疗饥过瘾,以为这就是欣赏文学。这是精神上的中毒,可以使整个的精神受腐化。
有些人知得不周全,趣味就难免窄狭,像上文所说的,被囿于某一派别的传统习尚,不能自拔。这是精神上的短视,“坐井观天,诬天渺小”。
要诊治三种流行的毛病,唯一的方剂是扩大眼界,加深知解。一切价值都由比较得来,生长在平原,你说小山坡最高,你可以受原谅,但是你错误。“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那“天下”也只是孔子所能见到的天下。要把山估计得准确,你必须把世界名山都游历过,测量过。研究文学也是如此,你玩索的作品愈多,种类愈复杂,风格愈纷歧,你的比较资料愈丰富,透视愈正确,你的鉴别力(这就是趣味)也就愈可靠。
人类心理都有几分惰性,常以先入为主,想获得一种新趣味,往往须战胜一种很顽强的抵抗力。许多旧文学家不能欣赏新文学作品,就因为这个道理。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起初习文言文,后来改习语体文,颇费过一番冲突与挣扎。在才置信语体文时,对于文言文颇有些反感,后来多经摸索,觉得文言文仍有它的不可磨灭的价值。专就学文言文说,我起初学桐城派古文,跟着古文家们骂六朝文的绮靡,后来稍致力于六朝人的著作,才觉得六朝文也有为唐宋文所不可及处。在诗方面我从唐诗入手,觉宋诗索然无味,后来读宋人作品较多,才发见宋诗也特有一种风味。我学外国文学的经验也大致相同,往往从笃嗜甲派不了解乙派,到了解乙派而对甲派重新估定价值。我因而想到培养文学趣味好比开疆辟土,须逐渐把本来非我所有的征服为我所有。英国诗人华兹华斯说道:“一个诗人不仅要创造作品,还要创造能欣赏那种作品的趣味。”我想不仅作者如此,读者也须时常创造他的趣味。生生不息的趣味才是活的趣味,像死水一般静止的趣味必定陈腐。活的趣味时时刻刻在发现新境界,死的趣味老是囿在一个窄狭的圈子里。这道理可以适用于个人的文学修养,也可以适用于全民族的文学演进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