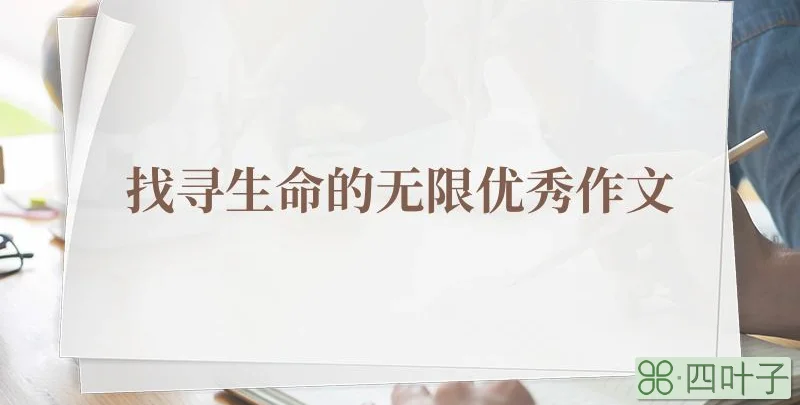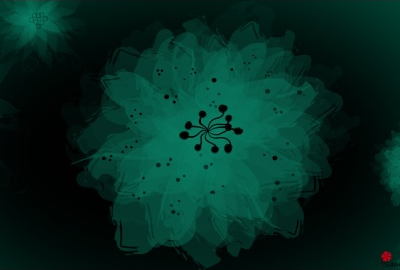找寻生命的无限优秀作文
帕斯卡尔对人有这样一种认识:人既伟大又悲惨。人认识到了自己所能取得的有限,不会诸事顺遂己愿,却仍渴望着无限,因生命中未得的残缺而不断追求。正因如此,未得的悲伤被巧妙地转化为追寻的快乐,这一份对无限的渴望使人清醒地定位自己,付出无悔的努力。
遥想当年《法国大革命史》这部巨着的形成过程,是着者卡莱尔在失去原稿,不复可得的悲惨遭遇中,重新鼓起勇气,再次完成,并更为精益求精的第二部成书。这部书是卡莱尔的梦想,是在一直渴望取得的顶峰。倘若就因一次失去的悲惨,认定此生无法企及,那卡莱尔何尝能在找寻未得,找寻无限的过程中重拾作为一个史学家的欣慰和喜悦呢?所以,对生命无限的渴望,对未知的那种期盼,恰是人们创作的不竭源泉。
纪伯伦曾指出:“一个人不在于他成就了什么,而在于他企求成就的东西。”在找寻生命的'无限中,人们练就了坚持不懈的品格,他们品尝了人世的悲欢,终于在找寻无限,追求未得中暂且放下了不圆满的缺憾,努力形成别具一格的伟大。的确,就算人在知、情、意方面总会有个限度,可这也提供了一个未得的契机,使自己突破已往的极限。
正如当年的培根,为了润色自己的随笔与人生箴言,时刻将笔记本放在身边,不断修改。或许在旁人眼中,那已经是足够完善的作品了,但培根认为他的文字还远未达到满意的标准。这也就激发他去不断超越自我,近于完美。
而今,当人们读着《培根随笔》时,是否品味出了那因“未得”而更上一层的语言?又是否体会到找寻未得,渴望无限所给予的活力和热忱?它确实融进了人的生命,让他们的的议论论文章都有了热度,让他们的智慧汇聚为文明的长河。从中,我们可以知悉人的伟大和悲惨了。没有得到心爱的东西,是有可悲之处,那是人终将走往的限度。
可当我们知晓了无限,进而追求和创造,在这一过程中,方显出生命的本色,达到更高的境界。其实,生命的意义也便是这样。从二律背反中清醒过来的人们,在得和未得间感慨不已,弱者安于所得,但强者找寻生命的无限,让卑微的生命铸成一座永恒的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