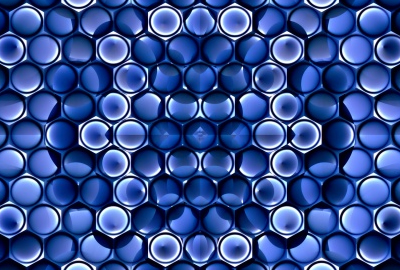人物传记3000字读书心得

很多年前,有人约稿,说是给青年学生推荐点文史类的经典,很多人写,然后凑成一本书。写什么好呢?约稿人说,你就拣历史方面自己觉得重要的书,随便写,字数在三千字左右,当然,最好通俗一点。我依命行事,临动笔,想了一下,在我心中,什么够得上“重要”二字?好像很多也很少,千挑万选,未必合适,为稳妥起见,还是写两本我比较熟悉也比较喜欢的书吧,一本是《史记》,一本是《观堂集林》。但文章写成,没有下文(眼下,这类书倒是大为流行)。
最近,承张鸣先生不弃,要我为《新东方》奉献小文,我素无积稿,翻箱倒柜,只有这点东西在。现在拿出来,真不好意思。书是很普通的书,话是很普通的话,难免老生常谈,重复别人讲过的东西。说不定,还有什么狐狸尾巴,让人抓住,也保不齐。我只能这么说,这两篇旧稿,除大家熟悉的事,有些问题,我是认真想过,其中还是有一点心得体会。我们先谈《史记》。读它,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是在和活人谈话。司马迁,好人。好人经常倒霉,我对他很同情,也很佩服,觉得他这一辈子没有白活。
《史记》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大家都知道,它是一部史书,而且是史部第一,就像希罗多德之于希腊,我们也是把司马迁当“史学之父”。但此书之意义,我理解,却并不在于它是开了纪传体的头。相反,它的意义在哪儿?我看,倒是在于它不是一部以朝代为断限,干巴巴罗列帝王将相,孳孳于一姓兴亡的狭义史书,像晚于它又模仿它的其他二十多部现在称为“正史”的书。我欣赏它,是因为它视野开阔,胸襟博大,早于它的事,它做了总结;晚于它的事,它开了头。它是一部上起轩辕,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的“大历史”。当时的“古代史”、“近代史”和“当代史”,它都讲到了。特别是他叙事生动,笔端熔铸感情,让人读着不枯燥,而且越想越有意思。
司马迁作《史记》,利用材料很多。它们不仅有“石室金匮”(汉代的国家图书馆兼档案馆)收藏的图书档案,也有他调查采访的故老传闻,包含社会调查和口头史学的成分。学者对《史记》引书做详细查证,仅就明确可考者而言,已相当可观。我们现在还能看得到的早期古书,它几乎都看过。我们现在看不到的古书,即大家讲的佚书,更是多了去。这些早期史料,按后世分类,主要属于经、子二部,以及史部中的“古史”。经书,其中有不少是来自官书旧档,年代最古老。它们经战国思想过滤,同诸子传记一起,积淀为汉代的“六艺之书”和“六家之学”。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我们从汉代思想进窥先秦历史的重要门径。不仅如此,它还涉及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包含后世集部和子部中属于专门之学的许多重要内容,同时又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总汇。
它于四部仅居其一,但对研究其他三部实有承上启下(承经、子,启史、集)的关键作用。借用一句老话,就是“举一隅而三隅反”。据我所知,有些老先生,不是科举时代的老先生,而是风气转移后的老先生,他们就是拿《史记》当阅读古书的门径,甚至让自己的孩子从这里入手。比如大家都知道,王国维和杨树达,他们的古书底子就是《史》、《汉》。所以,我一直认为,这是读古书的一把钥匙,特别是对研究早期的学者,更是如此。
读《史记》,除史料依据,编纂体例也很重要。这本书的体例,按一般讲法,是叫“纪传体”,而有别于“编年体”(如鲁《春秋》、《左传》、《纪年》及后世的《通鉴》)和“纪事本末体”(如《国语》、《国策》和后人编的各种纪事本末)。但更准确地说,它却是以“世系为经”,“编年”、“纪事”为纬,带有综合性,并不简单是由传记而构成,在形式上,是模仿早期贵族的谱牒。司马迁作史,中心是“人”,框架是“族谱”。它是照《世本》和汉代保存的大量谱牒,按世系分衍,来讲“空间”(国别、地域、郡望)和“时间”(朝代史、国别史和家族史),以及“空间”、“时间”下的“人物”和“事件”。它的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是讲“本”,即族谱的“根”或“主干”;“世家”是讲“世”,即族谱的“分枝”;“列传”是讲“世”底下的人物,即族谱的“叶”。
这是全书的主体。它的本纪、世家都是分国叙事、编年叙事,用以统摄后面的列传。本纪、世家之外,还有“十表”互见,作全书的时空框架。其“纪传五体”,其中只有“八书”是讲典章制度,时空观念较差,属于结构性描述。原始人类有“寻根癖”,古代贵族有“血统论”,春秋战国“礼坏乐崩”,但“摆谱”的风气更盛(“世”在当时是贵族子弟的必修课),很多铜器铭文,都是一上来就“自报家门”,说我是“某某之子某某之孙”。司马迁虽生于布衣可取卿相的汉代,但他是作“大历史”。他要打通古今,保持联贯,还是以这样的体裁最方便。这是我们应该理解他的地方。
司马迁作《史记》,其特点不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以“互文相足之法”,节省笔墨,存真阙疑,尽量保存史料的“鲜活”。比如初读《史记》的人,谁都不难发现,它的记述往往自相矛盾,不但篇与篇之间会有这种问题,就是一篇之内也能摆好几种说法,让人觉得莫衷一是。但熟悉《史记》体例的人,他们都知道,这是作者“兼存异说”,故意如此。它讲秦就以秦的史料为主,讲楚就以楚的史料为主,尽量让“角色”按“本色”讲话。这非但不是《史记》的粗疏,反而是它的谨慎。如果吹毛求疵,给《史记》挑错,当然会有大丰收,但找错误的前提,首先也是理解。
《史记》这部书伟大,它的作者更伟大。我们“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一定要读他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当然很重要,因为只有读这篇东西,你才能了解他的学术背景和创作过程,知道他有家学渊源、名师传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老道,所以文笔也老道。但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他还有一封《报任安书》。如果我们说《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学术史”,那么《报任安书》就是他的“心灵史”。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行将就死”之人的心灵对话,每句话都掏心窝子,里面浸透着生之热恋和死之痛苦。其辗转于生死之际的羞辱、恐惧和悲愤,五内俱焚、汗发沾背的心理创伤,非身临其境者,绝难体会。小时候读《古文观止》,我总以为这是最震撼人心、催人泪下的一篇。
司马迁为“墙倒众人推”的李将军(李陵)打抱不平,惨遭宫刑,在我看来,正是属于鲁迅所说敢于“抚哭叛徒”的“脊梁”。他和李将军,一个是文官,一个是武将,趣舍异路,素无杯酒交欢,竟能舍饭碗、性命不顾,仗义执言,已是诸、刿之勇不能当。而更难的是,他还能在这场“飞来横祸”之后,从命运的泥潭中撑拄自拔,发愤著书,成就其名山事业。读《报任安书》,我有一点感想:历史并不仅仅是一种由死人积累的知识,也是一种由活人塑造的体验。这种人生体验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贯穿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历史的共同精神。史家在此类“超越”中尤为重要。它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盈虚有数”的众多生命汇为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首先就在于,它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我想,司马迁之为司马迁,《史记》之为《史记》,人有侠气,书有侠气,实与这种人生经历有关。一帆风顺,缺乏人生体验,要当历史学家,可以;但要当大历史学家,难(我以为,“大历史”的意义就在通古今,齐生死)。
以个人荣辱看历史,固然易生偏见,但司马迁讲历史,却能保持清醒客观,即使是写当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肤之痛,也能控制情绪,顶多在赞语中发点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历史,写史和评史,绝不乱掺乎。
对司马迁的赞语和文学性描写,我很欣赏。因为恰好是在这样的话语之中,我们才能窥见其个性,进而理解他的传神之笔。例如,在他笔下,即使是“成者为王”的汉高祖也大有流氓气,即使是“败者为贼”的项羽也不失英雄相。就连当时的恐怖分子,他也会说“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就连李斯这样的“大坏蛋”,他也会描写其临死之际,父子相哭,遥想当年,牵黄犬,逐狡兔的天伦之乐。很多“大人物”写得就像“小人物”一样。
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有关,《李将军传》也值得一读(有趣的是,它是放在《匈奴传》和《卫将军传》的前边)。他讲李陵之祸,着墨不多,对比《汉书》,好像一笔带过。这种省略是出于“不敢言”还是“不忍言”,我们很难猜测。但他在赞语中说:
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司马迁说的“李将军”是李广而不是李陵,然陵为广孙,有其家风,就连命运的悲惨都一模一样。读者若拿这段话去对比一下苏建评卫青的话,所谓“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卫将军传》赞引),他的“无言”不是更胜于“有言”吗?
汉代以后,“卫将军”只见称于记录汉代武功的史乘,而无闻于民间。相反,李将军却借诗文的传诵而大出其名。1997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全国考古新发现精品展,其中有块敦煌市博物馆送展的西晋壁画砖(图一),上面有个骑马的人物,正在回头射箭,上有榜题为证,不是别人,正是李广其人。
看见“李将军”,我就想到了司马迁,想到了史学中的文学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