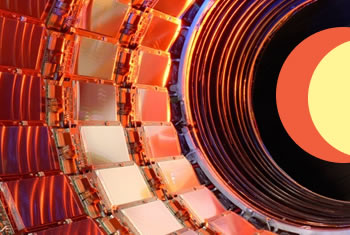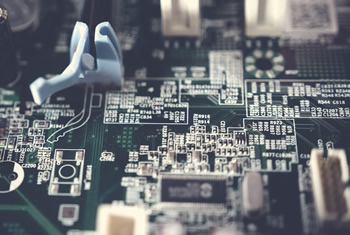唐诗二首读后感

今年看了两本书《蒙曼品最美唐诗:四时之诗》《蒙曼品最美唐诗:人生百味》,选它们读是因为年初看央视的《中国诗词大会》,觉得这位女教授容貌寻常,却很迷人。喜欢她的谈吐,豁达朴直,让人觉得舒适可亲,更喜欢她的才华,有一种谦和的渊博。
看了这两本书,我更是对蒙老师佩服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因为她品读唐诗,太美太雅太有趣了,字里行间,看得人汗毛都竖起来了,就是那种,又澎湃又舒服的感觉。因为你会发现,她不是在点评、在释义、在解析。她是在与诗人们谈天说地,而大唐的那些诗仙诗圣诗佛诗鬼们,都是她的朋友呢!
因为蒙曼老师,我深深的觉得对于古诗词的诵读应该分三个层次,第一,只是因为喜爱诗词的辞藻华丽,而附庸风雅的站在墙外,看热闹。第二,就是因为明白诗词的惊才绝艳,而心悦诚服的站在楼下,仰头望。第三,却是因为迈入诗词的真境之中,而心有戚戚的站在楼上,与往来古今千余年的文人们神交意往了。
也就是说,面对千古文华精粹,当我们还在心安理得的看热闹、仰头望时,蒙曼老师却早已经迈步上去,同诗词名篇的作者们往来谈笑了。
其实,我也是喜欢诗词的,虽然相比之下,我这点儿小小的喜欢,显得浅薄又微末。但我还是会大言不惭的说我喜欢诗词,因为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于我们的文化菁华,能喜欢、会欣赏,就是值得骄傲的事。
我爱古诗词,很早就喜欢,只是资质不够,毅力欠佳,所以,一直自得其乐的看看热闹、心安理得的仰脸膜拜。可是我想,我大概也有那么一两次时运特别好的时候,窥视到了那么一星半点的真意吧。
记得高中时的某个晚春,大庆一中校园里满院的丁香花,午后的一场急雨,压下了北方春季独有的热燥尘土气息,我坐在靠窗的座位,看着外面清凌凌的雨后校园、金澄澄的黄昏暮色,还有那急雨打落的一地的藕荷色丁香花瓣,我一下想起了几个月前,偶然记在脑子里的半阙词,“欲黄昏,雨打梨花深闭门。”因为这一瞬间的心思神往,窥探到词中的真意与美感,那整个晚上我都满怀着莫名的快意和不可言说的喜悦。这是古人馈赠给千年后的我,一个小女子的无价宝,这“无价宝”与“有情郎”一样,是古代话本里并称的人世稀罕物。
所以这么多年来,“欲黄昏,雨打梨花深闭门。”一直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诗词,这是一种无法诉与他人知晓的、充满奥义的美好。
还记得我最开始接触诗词,是在小说、作文选中,是在电视剧里。
那时看小说《天龙八部》,讲段誉从大理初到江南,面对着那里的江南风物、吴侬软语,他眯着眼惬意的说,“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远,斜日杏花飞。”
看作文选里,一个学生非常直莽的表达自己将来想当作家的愿望时,豁达又无畏,他说,“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看一个TVB的古装电视剧,女主角一边弹琵琶一边用粤语期期艾艾的吟诵,“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
那时诗词是我平凡生活中能接触到的吉光片羽,一两句话,就足够惊艳初见、咀嚼良久。之后,我会去找这句话出自哪里,整首的诗词是怎样的?能写出这么美丽诗句的诗人还写了其他的什么诗吗?我对诗词的了解就这样,由点到线,由线到面。而最初的那一个“点”是源自少年时一点点懵懂的喜爱。
后来毕业了,工作了,成家了,沉溺于忙碌又幸福的人间烟火气,诗词,曾经短暂的退出过我的生活。它的再次出现是和一个小名叫如意的小姑娘一起,而那个小姑娘呀,她是我的女儿。我想我的小姑娘也能了解诗词、喜欢诗词,希望她也能接受这份来自古人的慷慨馈赠,可以体会到千年间的瑰丽与曼妙。
诗词应该怎么去学,怎么去背呢?作为一个妈妈,我一直在琢磨、在尝试、在调整。一开始带着小小的如意背诗时,真的觉得这诗的题目是什么,作者是谁这些都不重要,就是让孩子在年幼时能对古典诗句产生亲近感,可以把满口金玉一样的词句揉进她童年的记忆里,这应该是一个对美产生感知的良好开端。
对于一个三四岁的小朋友来说,诗词的简短押韵、抑扬顿挫,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儿歌童谣,还记得那时的如意奶声奶气的背,“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真是叫人爱得不得了,用新嫩童稚的语调说出老旧沧桑的句子,这样的“反差萌”美得令人心折,你听不到诗中该有伤悲,却能看到古老的文化焕发出的澎湃力量。
和似懂非懂的小孩子一起读诗背诗,就会有一箩筐的有趣故事。记得有一年,我给如意讲一首诗的题目,“就是早晨起来从一个叫净慈寺的地方出来,送朋友林子安出门去外地。”讲完后,我给她念“《晓出净慈寺送林子安》宋。杨万里。”如意忽然打断我,“杨万里也是人的名字吗?”我说,“对呀!”如意非常疑惑的说,“古代人好奇怪,送两个人走为什么不一起说了?”她嘀嘀咕咕的重复,“送林子方、送杨万里……”小朋友的脑回路,真是可爱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