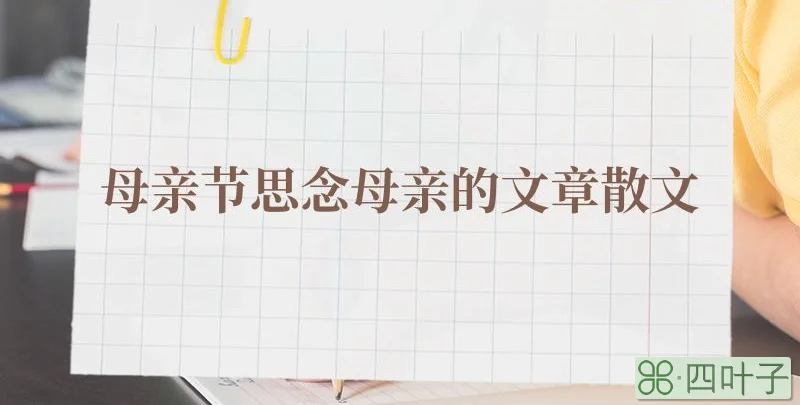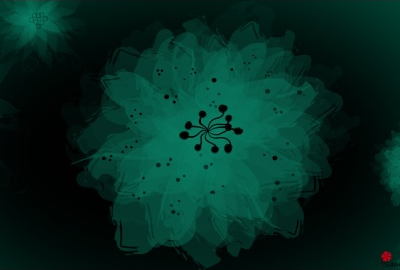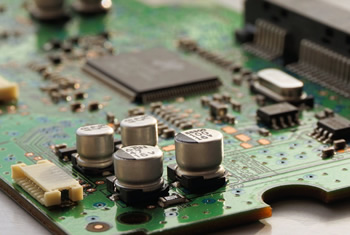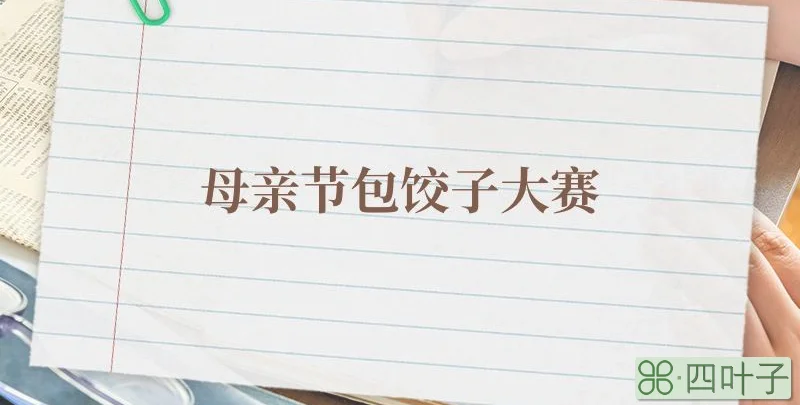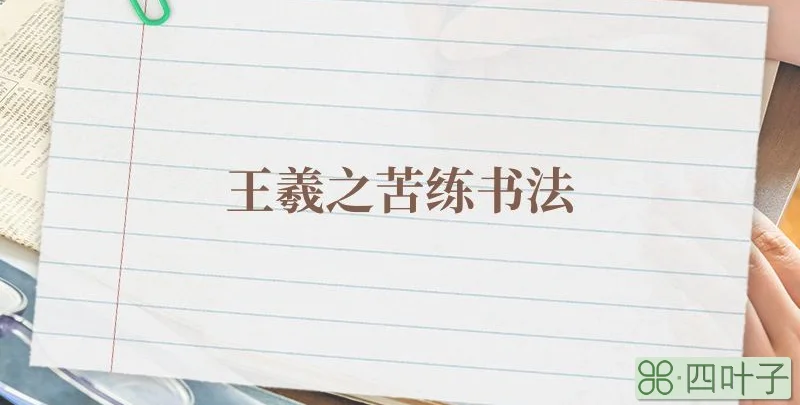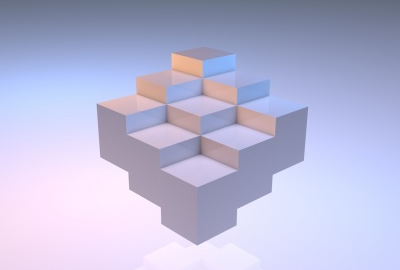母亲节思念母亲的文章散文
又是一年清明节。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间,母亲离开我们已经三年多了。母亲在,家在;母亲走了,家里总觉得缺少了许多。
母亲去世后,每次去看望父亲,走到家门口,总想喊一声妈走进屋里才蓦然惊觉,母亲已经走了。每每此时,总禁不住眼眶潮湿,一阵心悸。在邻居和亲人们的眼里,我们兄妹五人都是孝顺的,但比起母亲的孝道来,我知道我们还差得远。
父亲在兄妹六人最小,母亲嫁给父亲的时候,爷爷已经岁数很大了。当时家里只有间半草房,一间住室,半间灶台。新婚的父母只能和爷爷住在一间屋子里,一住就是十年。
十年里,母亲从未嫌弃过爷爷。冬天让爷爷住炕头;夏天让爷爷住炕梢。早晨的第一盆洗脸水打给爷爷;饭熟了,第一碗饭先盛给爷爷。
在爷爷病重弥留之际,母亲从盐罐底扒拉出两片肉,用小铁勺在灶口煎好,任凭我怎样央求也没舍得给我吃一小口,全部捣碎喂给了爷爷。爷爷活到八十八岁,在缺食少医的六十年代,绝对称得上是高寿。在爷爷的最后十年里,浸透着母亲多少贤惠和孝道啊!母亲去世时,尚健在的姑姑告诉我,她梦见我爷爷了,梦里的爷爷开心的笑着,是为了能和他贤惠的儿媳见面吧我有一个坏脾气,工作中见不得人喊苦喊累,有时甚至为此伤了和气。
经常有人问我,工作忙吗?累吗?我总是说不。因为我知道,比起母亲一生的辛苦劳累,我工作和生活中的一点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林徽因曾写道:死是悲剧的一章,生则是一场悲剧的主干。用来形容母亲的一生十分贴切。
母亲命运坎坷,多历磨难。她三岁时,身为抗日骨干的姥爷被汉奸杀害,幼年失怙;少年时溺水,幸脱大难;上山拾柴曾遭遇野狼,惊吓惶恐;中年时患上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彻夜难眠,精神错乱,几近疯癫;年纪大时,哮喘严重,稍微一累便喘得厉害在艰难的岁月里,母亲用赢弱的身躯支撑着这个家,庇护着我们长大。母亲心灵手巧。
我也能下厨房,做出的饭菜也常常得到朋友的褒奖。但我做的红烧肉,怎也做不到母亲的入口即化、香而不腻的程度。每每面对满桌肴馔,也总是怀念母亲红烧肉的味道。
小时候,端午节弟弟妹妹身上的荷包、春节时窗户上的窗花,细致精巧,堪称艺术品,它们都出自母亲粗糙的双手。母亲的手工,给贫寒的日子平添了几分温馨和乐趣。我们兄妹五人,吃穿用度全凭母亲的一双巧手。
家境贫寒,衣服鞋袜难免缝缝补补的,但母亲总能让我们都能穿上可体应季的衣服。上初中的时候,军装可称得上是奢侈品,那诱人的军绿让人垂涎不止,谁要是能穿上一件军衣别提多荣耀了。母亲看透了我的心思,东挪西借,从供销社扯来一块军绿布,仔细剪裁,细密缝制,给我做了一身漂亮的军服。
穿着上学,同学们都惊讶地围着我,追问谁送给了我一身军装?我告诉同学们是母亲手工缝制的,他们那羡慕的神情让我得意极了。母亲一生坚强。那年我因车祸受伤,右臂骨肉粉碎,几近截肢。
住院期间,伤痛让我彻夜难眠,同病室的伤者呻吟呼号,只有我一声不吭,连止痛药几乎都不吃。人们都说我能扛,可他们哪里知道,我骨子里流淌着的是母亲的血液。母亲辛苦劳累了一辈子,饱经风霜,承受疾病和贫困的苦难。
从没有过抱怨和妥协,可以说母亲的一生是与命运抗争的一生。即使生命的最后阶段也体现了母亲的坚强!母亲在世的最后三、四年,她经历了两次脑出血。第一次,在母亲的坚韧毅力下,身体基本康复。
她努力地锻炼自己,自理生活,生怕给我们增添一点负担和麻烦;第二次脑出血出院后,她也总想努力地让自己站起来。每次搀扶着母亲,看着她咬着嘴唇,艰难地想迈开步子时,我总是热泪盈眶。若不是母亲同时患上了真红细胞增多症,我坚信母亲一定能再次站起来。
母亲爱我们。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兄妹五人很少被母亲呵斥,我们在母亲的疼爱中长大。唐山大地震时,我们从睡梦中惊醒,母亲用手护着我们的头,说:没事的、没事的母亲每次病重,她都坚强地说:我不能死,我怕你们成了没妈的孩子。
我离家最长的时间是读师范的两年。母亲怕我在学校吃不饱,我每次离家上学,她总是给我带上一包亲手做的油炒小米面。母亲做的油炒面,色泽金黄,不生不糊,放上点糖,开水一沏,可算得一道美食。
现在偶尔从超市买回的油炒面,比母亲的味道差得远了。我爱吃烙饼,在少肉缺油的年代里,母亲烙的白面饼很厚,层数很多,外皮酥脆,里面软熟,很是好吃。在我上班后,每次回家,母亲总是给我烙饼,稍微时间长一点不回家,母亲就烙上几块饼,让父亲风尘仆仆赶到县城送给我子欲养而亲不待。
母亲啊,你为什么不多在世几年呢?2013年农历八月二十四晨七时,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母亲走时,流下了两行热泪,我知道,她深深地眷恋着这个世界,深深地眷恋着我们。我知道,她多想再享受几天这迟到的晚年幸福生活站在母亲的坟前,依稀觉得母亲的音容宛在;而纸钱燃起的缕缕青烟,让我真切地感受到母亲已经走了。
我再也听不到母亲喊我的乳名,一声轻轻的呼唤吃饭了。一个地下、一个地上;一个里头、一个外头;阴阳两隔,永不相见!去年调零的花朵,今年就要再次绽放,而我的母亲呢?抬头望望天空,澄澈高远。我忽然想,如果真有地狱和天堂的话,母亲一定在天堂里,微笑着看着我们,佑护着我们母亲,天堂里的母亲,安好!【怀念母亲】母亲的娘家是在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
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土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当巡察的。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须下地作活。
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功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之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而我的大甥女还长我一岁啊。
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哥与我。我是老儿子。生我的时候,母亲已四十一岁,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
由大姐与二姐所嫁入的家庭来推断,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里,大概还马马虎虎的过得去。那时候定婚讲究门当户对,而大姐丈是作小官的,二姐丈也开过一间酒馆,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可是,我,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我生下来,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感谢大姐,把我揣在怀里,致未冻死。
一岁半,我把父亲克死了。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力抚养了。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鸦片,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
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
她作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
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久已残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
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
与母亲相依如命的是我与三姐。因此,她们作事,我老在后面跟着。她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她们扫地,我就撮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
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可是,殷勤的给他们温酒作面,又给她一些喜悦。
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到如今为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姑母时常闹脾气。
她单在鸡蛋里找骨头。她是我家中的阎王。直到我入中学,她才死去,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
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命当如此!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这样说。是的,命当如此。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
她最会吃亏。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她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少妇们绞脸凡是她能做的,都有求必应。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
她宁吃亏,不逗气。当姑母死去的时候,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承继权,母亲便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烂板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肉鸡也送给他。
可是,母亲并不软弱。父亲死在庚子闹拳的那一年。联军入城,挨家搜索财物鸡鸭,我们被搜两次。
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等着鬼子进门,街门是开着的。鬼子进门,一刺刀先把老黄狗刺死,而后入室搜索,他们走后,母亲把破衣箱搬起,才发现了我。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压死了。
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北平有多少变乱啊,有时候兵变了,街市整条的烧起,火团落在我们院中;有时候内战了,城门紧闭,铺店关门,昼夜响着枪炮。这惊恐,这紧张,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儿女安全的顾虑,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受得起的?可是,在这种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
她的泪会往心中落!这点软而硬的性格,也传给了我。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当作当然的。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画好的界限。
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敢不去,正像我的母亲。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二十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当我在小学毕了业的时候,亲友一致的愿意我去学手艺,好帮助母亲。我晓得我应当去找饭吃,以减轻母亲的勤劳困苦。可是,我也愿意升学。
我偷偷的考入了师范学校制服,饭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只有这样,我才敢对母亲说升学的话。入学,要交十元的保证金,这是一笔巨款!母亲作了半个月的难,把这巨款筹到,而后含泪把我送出门去。
她不辞劳苦,只要儿子有出息。当我由师范毕业,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我只说了句: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
我入学之后,三姐结了婚。母亲对儿女都是一样疼爱的,但是假若她也有点偏爱的话,她应当偏爱三姐,因为自父亲死后,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亲和三姐共同撑持的。三姐是母亲的右手,但是母亲知道这右手必须割去,她不能为自己的便利而耽误了女儿的青春。
当花轿来到我们的破门外的时候,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的凉,脸上没有血色那是阴历四月,天气很暖,大家都怕她晕过去。可是,她挣扎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看花轿徐徐的走去。不久,姑母死了。
三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学校,家中只剩母亲自己。她还须自早至晚的操作,可是终日没人和她说一句话。新年到了,正赶上政府倡用阳历,不许过旧年。
除夕,我请了两小时的假,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母亲笑了。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她楞住了。
半天,她才叹出一口气来。到我该走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是那么热闹,我却什么也没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今天,泪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当日孤独的过那凄惨的除夕的慈母。
可是,慈母不会再候盼着我了,她已入了土!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投下的轨道一直前进的,所以老人总免不了伤心。我廿三岁,母亲要我结婚,我不要。我请来三姐给我说情,老母含泪点了头。
我爱母亲,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时代使我成为逆子。廿七岁,我上了英国。
为了自己,我给六十多岁的老母以第二次打击。在她七十大寿的那一天,我还远在异域。那天,据姐姐们后来告诉我,老太太只喝了两口酒,很早的便睡下。
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说出来。七七抗战后,我由济南逃出来。北平又像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可是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却跑到西南来。
母亲怎样想念我,我可以想像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详的消息。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
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我怕,怕,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告诉我已是失去了根的花草。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老母的起居情况。我疑虑,害怕。我想像得到,没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
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使我不再疑虑。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劳军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
我不敢拆读。就寝前,我拆开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
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