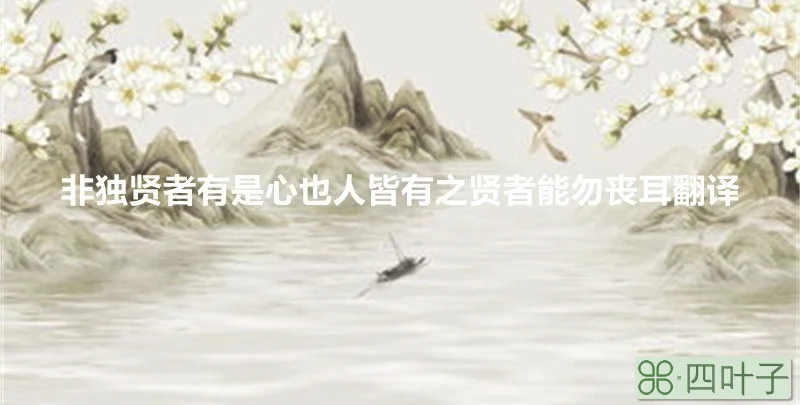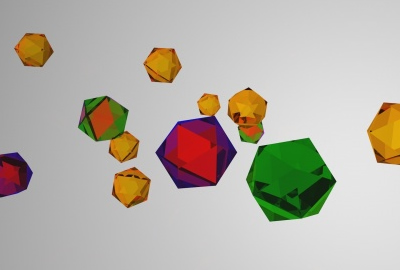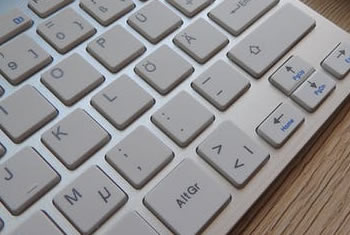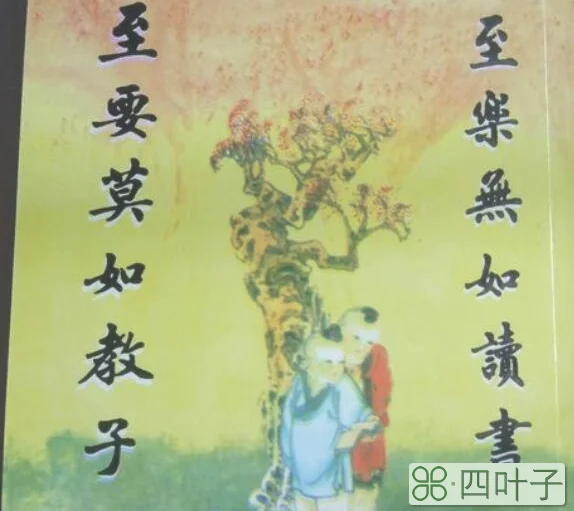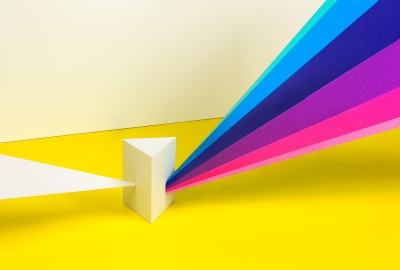读孟子后的收获和感想

感触最深的是《告子上下》这篇,在阐述行善论的学说。第一,人性本是善。孟子说:“人之性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有无不下。”人的性善,是普遍的共同属性。 首先,孟子性善说的第一个问题,是没对“善”做出清晰界定。在其著作中,无法找到善的确切含义,对善的所指需要通过相关论述去把握。张奇伟提出,之所以能使不同观点的人在不做界定条件下同以善恶谈人性,是由于人们对善恶指代已取得了相当一致,至少都认为“善”是在指仁慈、宽惠、清廉等德性和德行,而且还说明孟子的“善”指的首先是仁、义、礼、智诸德性和德行,然后是人的优秀性,最后是一种可以满足人需要的价值[2]10。这虽不失为一个对善的很好归纳,但仍无法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善的内涵。
其次,遇到的问题会是孟子把义和利完全对立,崇尚义反对利,却没能指出如何确定义与不义,仅让人去求助内心。这可从他谈的“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孟子·尽心上》),和答梁惠王时的“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梁惠王上》),以及谈到善端时的“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告子上》)中进行理解。张岱年就提出孟子之尚义反利,更甚于孔子,并将义与不义之辨别标准诉诸良能和良知[1]387-388。无疑,这正是孟子观点之贴切反映,而该观点则不但使其性善说掉进唯心论泥沼,也无形中把利与善分割。 再次,在人我关系上,孟子沿用了人我对立模式。焦国成指出,我国古代人我关系思想中人与我对称,这里的“人”指的是我以外和我产生关系且与我具有一样意识的他人。在说到儒家仁爱论后,还特别强调,在孔子用“爱人”来要求之人我关系思想中,“爱人”的“人”,指的是所有我以外的人。不能由于我也属人类,从而将“爱我”说成“爱人”。反之同样,不能把“爱人”歪曲为爱我[3]153。显然,孟子性善说作为孔子仁爱观点的延续,仍沿用着人我对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