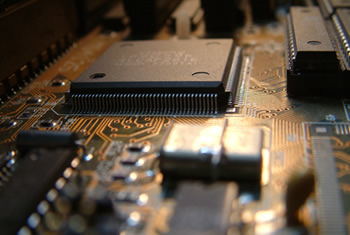一个人的遭遇续写

如果硬是要说点什么的话,我想讲2009年我跑到家乡而非神农架呆了一年。于是后来有了一些关于湖泊生活的故事,比如野猫湖。在故乡的田野上自由行走,对许多所谓成名作家是件奢侈的事,为了对自己身份的显摆,不可能独自去重温旧梦,再一次吹吹童年的野风。我庆幸我不属于这类作家。我是个比较不太在意这个世界的人,不会认为自己到了何种需要尊重的地步。回到故乡,就像一个在外干了些杂事又回来过日子的人一样。我怀着一种不被人注意的窃喜,独霸了故乡某一天的田埂与湖水。重新像回到儿时一样打量她。水的气息,庄稼和野草的气息,人与畜的气息,村庄的气息,甚至夕阳的气息,都是好闻的,并且不想与人分享。谈不上感恩,谈不上思乡,谈不上热爱,就是回来走走,没有目的。就像那些鱼类,非得要万里迢迢回到它出生的地方去产卵。写小说也是产卵的方式吧。我所做的一切,分析起来,不过就是一种基因密码,如此而已。
但人不是鱼,人还有思想,人对他所有经过的地方会有对比,会有感悟,会思考这里与那里有何不同,为什么会是这样,这里的人为什么会吃这种饮食,会这么讲话,为什么会有这些与他人不同的记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出生和死亡(比如风俗)等等。这个地方孕育了我和我们的过去,还将孕育更多的人和更久的以后。她的生活如此漫长柔韧,有什么道理?有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合理的?哪些是要痛哭的,哪些是应该欢笑的?
关于小说,大约就是这一些无头绪的的东西吧。就像一堆从臭水中沤过许久的麻秆上扒出来的麻,乱七八糟,你把有用的,梳理一遍,编织出了你需要的物品。当然可以编织成任何东西,但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喜好,编出他认为最有趣最好看最有意义的东西。
我们所处的生活,我们的审美,我们认为的时尚,全都在改变,世界在不断的沧海桑田中轮回。许多的水面没有了。不急,也许哪一年一个大地震一次大洪水,又会有一个大湖出现。有的正在隆起,有的正在坍陷;有的鸿沟正在填平,有的深渊愈来愈瘆人;漂亮的村庄在荒芜,荒芜的田野成为了城镇。
没有不变化的,沙漠也在改变形象。我的小说也是在变化,我不会成为僵死的标本,因为我在不断地行走和写作。我知道我的脚让我获得了新生,永远有泥巴在脚上,晚上再清洗鞋子,还带回一些过去曾忽略的植物。现在知道了它们的名字,它们的少年、盛年和老年。还知道了一些庄稼。过去我伏在它们中间,但并不十分了解它们。现在我与它们像彬彬有礼的客与主,可以探听一些陈年旧事,细看它们,不再是一个靠它们的产出养活的人。这是很好的事。我已经有了与它们对话而不是被它们奴役的权利。这是年龄赐予我们每个人的恩典。因为我们努力过,所以我们成为了田野的散步者,也成为了田野的生客、观察者和记录者。当然,我们会成为田野的亡灵,会在故乡游荡。我坚信,我们的作品也将永远在故乡的田野上游荡。
感谢那些饮食和水。我现在变得如此温和。我的这个后记就是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