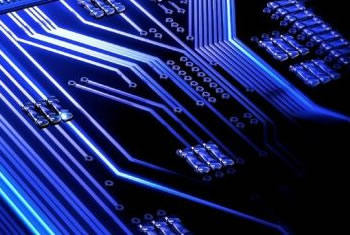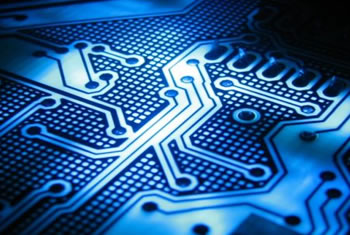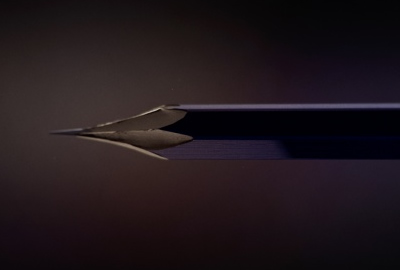散文二篇原文

海员烟斗
如其我画Whitman或Maiakowski的像,我一定要在他们的宽大的唇边加上一个海员烟斗——不管他生前曾否有一个海员烟斗。
那样一定是显得酷肖的:在事务所临街的大窗口,或是群众的会集里,或是演讲坛口,或是咖啡店当中……
也或者是航轮的舱板上,喜悦于远旅的巨姿屹立着,两臂叉在胸前,衬衫该是解开的……而海上有强烈的风。
厚发像平野遇上暴风雨前的麦浪般起伏着,眼望着那遥阔的彼方……
天穹之下是静寂的……
烟斗里喷出的白烟,随浪声往后远游……
一种东西,必须属于有同样情调的人的。
为了大集团的朗诵的嘴像海洋般张开着,我要在他们的画像中加上这征象着cosmopolite情感的,它的白烟像最新鲜的诗句般流向全世界的海员烟斗啊。
灰色鹅绒裤子
好像我没有到这世界上来之前,我曾穿过这裤子的……
那是一种出奇的灰色,淡的,柔性的……就是这样,你会想起了一双眼睛,一双为热情所磨折了的,柔性的,淡的,灰色的眼睛。
人们的视线都集中在裤子上,当人们和我相遇的时候。于是,我知道这裤子对于人们是陌生的——像一阵遥远的,回忆般遥远的,从天外吹拂来的风。
这天外的风,无定向的流着……
我一年四季都穿它……
它为我款待了几个不嫌避我的友人,它说出我缄默了的话语,它替我在地图上画了几条和它一样颜色的旅线……
它的每缕条纹里都映出:我无终止的散步的街,我的浓雾的早晨,到没有目的的地方去的早晨……
它的每缕条纹里每沾有那些码头的,车站的,一切我到过的地方的尘土的气息。
于是,在它对于人们是陌生的日子,被我爱了。
它于我是这末的亲切,像一切的颜色之于和它相同的颜色是亲切的一样;它是我的颜色!那末的淡,那末的飘忽,那么的无关心……
我走着……
好像我没有到这世界上来之前,我已经穿了这:灰色的,淡的,柔性的,永没有太阳的天上的云一样的裤子——天鹅绒的裤子的……
那末,你不认得我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