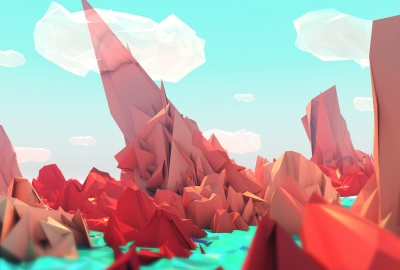曹禺对《雷雨》的评价

蛮性的遗留
我不知道怎样来表白我自己。我素来有些忧郁而暗涩;纵然在人前我有时也显露着欢娱,在孤独时我又是许多精神总不甘于凝固的人,自己是不断地来苦恼着自己。我是一个不能冷静的人,谈自己的作品恐怕也不会例外。我爱着《雷雨》如欢喜在融冰后的春天,看一个活剌剌的孩子在日光下跳跃,感觉如在粼粼的野塘边偶然听得一声蛙叫那样的欣悦。我会呼出这些小生命是交付我有多少灵感,给予我若何的兴奋。
这一年来批评《雷雨》的文章确实吓住了我,它们似乎刺痛了我的自卑意识,令我深切地感触自己的低能。我突地发现它们的主人了解我的作品比我自己要明切得多。他们能一针一线地寻出个原由,指出究竟,而我只有普遍地觉得不满,不成熟。每次公演《雷雨》或者提到《雷雨》,我不由己地感觉到一种局促,一种不自在,仿佛是个拙笨的工徒,只图好歹做成了器皿,躲到壁落里,再也怕听得顾主们恶生生地挑剔器皿上丑恶的花纹。
《雷雨》对我是个诱惑。与《雷雨》俱来的情绪蕴成我对宇宙间许多神秘的事物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它可以说是我的“蛮性的遗留”,我如原始的祖先们对那些不可理解的现象睁大了惊奇的眼。我不能断定《雷雨》的推动是由于神鬼,起于命运或源于哪种显明的力量。情感上《雷雨》所象征的,对我是一种神秘的吸引,一种抓牢了我心灵的魔。《雷雨》所显示的,并不是因果,并不是报应,而是我所觉得的天地间的“残忍”。
相关内容
-
囚绿记是高中还是初中
囚绿记是高中还是初中,,《囚绿记》是人教版高- -年级必修 二第一单元的最后一 -篇课文, 属于自读课。这个单元的课文都围绕“绿”这一主题, 或描写,或说明,极尽赞美“绿”之精神。可见编者是想要通过谱写绿色生命赞歌,提高学生感悟美,感悟生命的能力。此文讲述了作者与常春藤绿枝条的一段"交往"经历,描绘了绿枝条的生命状态和"性格特点",也写出了作者的生存状况和真挚心愿,含蓄地揭示了华北地区人民面临日本...
-
荆轲刺秦王爱国情怀
荆轲刺秦王爱国情怀,,表达作者赞扬荆轲机智勇敢和扶弱救困、反抗侵伐的侠义行为,表现作者反抗强暴统治的思想。《荆轲刺秦王》出自《战国策·燕策三》,记述了战国时期荆轲刺秦王这一悲壮的历史故事,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况,表现了荆轲重义轻生、为燕国勇于牺牲的精神。文章通过一系列情节和人物对话、行动、表情、神态等表现人物性格,塑造了英雄荆轲的形象。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战国末年,秦国代表的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
-
小二黑结婚课文故事梗概
小二黑结婚课文故事梗概,,在那个封建年代,家长制非常严重,小二黑的父亲二诸葛和小琴的母亲三仙姑,极力反对他们的结合。小二黑和小芹冲破封建传统和落后家长的重重阻挠,终于结为美满夫妻的故事。在封建社会的旧中国,青年人的婚姻,都是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封建思想的精神枷锁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谁也不敢自由恋爱。因此,他们的恋爱遭到小芹父亲二诸葛,母亲三仙姑的严历反对。冲破封建传统和守旧家长的阻挠,最终结为夫妻...
-
地心游记读后感
地心游记读后感,,1、《地心游记》读后感,我读了被誉为“科学时代的预言家”凡尔纳早期著名的科幻小说《地心游记》。《地心游记》发表于1864年,主要讲述了德国汉堡的里登布洛克教授受十六世纪冰岛学者阿尔纳的一封密码信的启发,和侄子阿克赛尔、向导汉斯,进行了一次穿越地心的探险旅行。读了这本书,我知道了不管做什么事,都要有冒险精神和坚持不懈的精神,这样才能成功。2、这个故事让我感受最深的是里登教授的冒险精...
-
读后感100多字三年级
读后感100多字三年级,,1、《老人与海》我读了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十分佩服小说中老渔夫的意志,他让我懂得了一个人一定要有坚持不懈的精神,才能获得成功。 小说描写的是一个年近六旬的老渔夫,在一次单身出海打鱼时,钓到了一条大鱼,却拉不上来。老渔夫同鱼周旋了几天后,才发现这是一条超过自己渔船数倍的大马林鱼,虽然明知很难取胜,但仍不放弃。后来又因大马林鱼伤口上的鱼腥味引来了几群鲨鱼抢食...
-
祝福读后感100字
祝福读后感100字,,《祝福》读后感《祝福》由“我”的口吻介绍了鲁四老爷家曾经的仆人祥林嫂的悲惨的一生。祥林嫂先后失去了两任丈夫,儿子被狼叼走,使得她精神出现了问题,手脚也不在麻利,变得迷信。一系列的行为使其被赶出了鲁家,以乞讨为生。最终,在一片祝福声中死去……祥林嫂是可怜的。两任丈夫,儿子先后去世,有这样遭遇的人,她一定是可怜的,但同时她也是可恨的。她不应该把自己的遭遇一遍遍的讲述了别人,以求博...
-
万能读后感开头精段落
万能读后感开头精段落,,1、“一根筷子容易折,十根筷子抱成团”,这话不错,在巨大的困难面前,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而许许多多个人汇集成集体,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最终赢得胜利2、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读完了《鲁滨逊漂流记》这本书。我佩服鲁滨逊活下去的意志,佩服鲁滨逊那顽强不屈的精神,被它感动了,被它震撼了,这是心灵的震动,心灵的呼唤。3、这几天我在读《80天环游地球》这本书,读着读着,我不知...
-
老猎狗读后感20字
老猎狗读后感20字,,道理:生老病死是世上万物都不可抗拒的规律,在这短促的人生旅途中,我们要知恩图报,用爱心播种希望,用真诚收获完美。《老猎狗》讲述了一条老猎狗年轻从未向森林中任何野兽屈服过,年老后,在一次狩猎中,遇到一头野猪,它扑过去咬住野猪的耳朵。它的牙齿老化,没有牢牢咬住,野猪逃跑了,它的主人骂了它一顿。猎狗说主人啊!这不能怪我不行。我的勇敢精神和年轻时是一样的, 但我不能抗拒自然规律。从前...
-
精神的三间小屋课后生字拼音
精神的三间小屋课后生字拼音,,具体如下:1、自惭形秽(huì):形秽:形态丑陋,引申为缺点。因为自己不如别人而感到惭愧。2、襟(jīn)怀:胸襟;胸怀;心胸。3、广袤(mào):土地的面积。东西的宽度为广,南北的长度为袤。4、驰骋(chěng):骑马奔跑;奔驰;自由地或随意地到处走动;漫游。5、坍(tān)塌:崩塌。6、形销骨立:形容身体非常消瘦。文章结构:第一部分(1~6):引出话题——如何布置...
-
爱国主义书籍读后感600字
爱国主义书籍读后感600字,,轻轻翻开飘着淡淡墨香的纸张,一阵激动。哦,那不仅是激动,那也是一种爱国。顺着文字铺开的小路,领悟战争年代的爱国……《小桔灯》反映了1945年抗战期间革命者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艰难处境和对光明,美好安定的生活的向往,赞扬了这些革命者的镇定自若,英勇无畏和乐观的精神。《小桔灯》的主人公是一位地下工作者的女儿。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残忍地逮捕和屠杀地下党,白色恐怖笼罩着重庆。小...
-
一块奶酪主要内容
一块奶酪主要内容,,1、该文围绕一块奶酪,讲述了一位以身作则的蚂蚁队长的故事。蚂蚁队长下令“搬运粮食,只许出力,不许偷嘴。谁偷了嘴,就要受到处罚”。当大家齐心协力搬运一块诱人的奶酪时,不小心拽掉了奶酪的一角。大家都非常渴望得到奶酪渣子,包括蚂蚁队长。最后蚂蚁队长两次忍住不偷嘴,命令年龄最小的一只蚂蚁吃掉奶酪渣。蚂蚁队长以身作则、关爱弱小的精神感动了大家,大家的干劲更足了。2、扩展资料:《一块奶酪》...
-
一块奶酪50字
一块奶酪50字,,课文围绕一块奶酪,讲述了一位以身作则的蚂蚁队长的故事。蚂蚁队长下令“搬运粮食,只许出力,不许偷嘴。谁偷了嘴,就要受到处罚”。当大家齐心协力搬运一块诱人的奶酪时,不小心拽掉了奶酪的一角。大家都非常渴望得到奶酪渣子,包括蚂蚁队长。最后蚂蚁队长两次忍住不偷嘴,命令年龄最小的一只蚂蚁吃掉奶酪渣。蚂蚁队长以身作则、关爱弱小的精神感动了大家,大家的干劲更足了。...
-
不懂就要问教学反思优点不足改进措施
不懂就要问教学反思优点不足改进措施,,《不懂就要问》是人教版小学语文第三册的一篇选读课文,讲的是孙中山小时候在私塾读书,敢于独立思考,敢于质疑,为了弄懂书里的意思,不怕先生的惩罚,大胆地向先生提出问题的事情。课文赞扬了孙中山认真读书、勤学好问的精神。在这里我也来谈论谈论我对物理这一科目的学习经验物理这一科目在初中分值对于我所在的江西是100分值的,也是一科很重要的科目,对于高中,是采用理综制度的,...
-
《复活》读后感300字
《复活》读后感300字,,小说名曰《复活》,它隐喻一个人泯灭的良知在某种精神力量的感化下能够获得重生。男女主人公透过各自的忏悔和宽恕,双双走向精神和道德的“复活”,使其人性得以复归,这一切带有浓厚的“不以暴力抗恶”和“道德的自我完善”的托尔斯泰的味道。他借此从社会和个人的道德角度对政府、法庭、监狱、教会、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作了深刻的批判,也让每一个读者思考个人道德和社会道德之间的关联,思索怎...
-
诗词三首9年级
诗词三首9年级,,行路难(其一)唐·李白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唐·刘禹锡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水调歌头...
-
牛郎织女二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
牛郎织女二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牛郎织女(二)》教学反思本文是牛郎织女故事的后半部分。本文叙述牛郎织女婚后美满生活和织女被王母娘娘无情地抓回天宫等事,歌颂了劳动人民反对压迫、争取自由幸福的精神, .反映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这段故事同上- -段故事-样,在表达上采用十分通俗的语言,叙述如行云流水。在内容上,上一课和本课连起来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本课以织女的经历(婚后生活- -一 被王母抓...
-
第一朵杏花是谁写的
第一朵杏花是谁写的,,佚名。《第一朵杏花》是一篇物候学的小故事。课文主要写了我国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前后两次向孩子问询第一朵杏花开放的具体时间,并且郑重记下的故事,赞扬了他严谨细致的科学态度、一丝不苟的研究精神、平易近人的处世原则。《第一朵杏花》说明只有通过精确、细致的观察,才能掌握事物变化的规律。意在让学生学习竺可桢在科学探究中一丝不苟的态度,培养学生细致观察周围事物的习惯。课文按时间先后顺序,分为...
-
青山不老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
青山不老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青山不老》是一篇略读课文,文章脉络清晰,重点突出,即通过了解老人创造的奇迹,理解青山不老的含义,感受老人与青山共存的精神。课上完了,反思自己的教学,有以下感受。一、课题引入,找准切入口课前,我先板书出示“老”字,请同学们来说说“老”的意思,然后自己有叫了在《说文解字》种这个字的意思,再引出“默读课文,你从哪些词句中感受到老人确实年岁大了,老了?”根据学生的回答,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