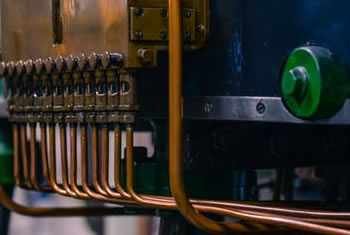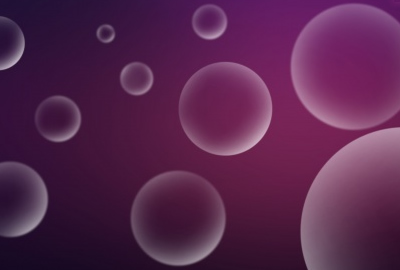山西腌菜-交口县特产山西腌菜
 山西腌菜有酵、酱制法。酵制的称酸菜,《周礼》称“菹”或“齑”(切碎腌),北魏《齐民要术》记有腌渍酸菜多种方法,山西民间有此传承。晋南村野,人们习惯将萝卜叶切碎,白萝卜擦丝,一层叶一层丝密密实实地压进缸里,于房檐下日月柔光的抚慰中和小雪大雪的冰冷里,慢慢地发酵成菜,直到冬至就可开吃。萝卜酸菜助消化、减油腻、调脾胃,苦日子里略加调拌配窝窝头,条件好一点与牛肉同炒佐白面馍馍,有时还包成饺子,融进一份生活从辛酸到香甜的记忆。
山西腌菜有酵、酱制法。酵制的称酸菜,《周礼》称“菹”或“齑”(切碎腌),北魏《齐民要术》记有腌渍酸菜多种方法,山西民间有此传承。晋南村野,人们习惯将萝卜叶切碎,白萝卜擦丝,一层叶一层丝密密实实地压进缸里,于房檐下日月柔光的抚慰中和小雪大雪的冰冷里,慢慢地发酵成菜,直到冬至就可开吃。萝卜酸菜助消化、减油腻、调脾胃,苦日子里略加调拌配窝窝头,条件好一点与牛肉同炒佐白面馍馍,有时还包成饺子,融进一份生活从辛酸到香甜的记忆。腌酸菜晋北民间多用长白菜。白菜古称“菘”,是菜之美者,有“春初早韭,秋末晚菘”(《南史》)之称。白菜好吃,但过冬不易,大同民间就制成酸窝菜:去黄叶、净水洗、开水烫,冷却后码进缸内,撒上花椒、红辣椒、小茴香、食盐等,注入凉白开水,再以净石压紧,放阴凉处发酵2个月即可食用,酸甜利口,清淡实惠。若以之氽白肉、煲鲤鱼,俱成佳味。雁北农户还腌制一种什锦酸菜,与德法洋人暗合,用甘蓝做原料,无处寻求杜松子,却掺入芹菜丝、胡萝卜丝,亦成其美。德法的酸甘蓝丝在法式大餐上,要配以熏猪蹄用金刀银叉来吃。雁北农户则水津津夹出几筷,就小米粥、山药蛋,闷头猛吃,有一股北路梆子的粗犷与豪气。
在晋中,平定黑豆叶腌酸菜从尧帝“黎藿之羹”(《中国历代御膳大观》)起,经过了那些“抱瓮聊度日,尝羹谋岁卒”(清代李正元《豆叶吟》)年代,已融入了家乡风土食俗的深厚感情。平定秋后做过冬准备,沤豆叶酸菜必为重要一项:采回豆叶,切丝氽透,凉水过凉,入大筐内上压青石挤干水分,然后再放入瓮里捣实,压上石头,添入清水、米汤待慢慢沤制。这样腌制的黑豆叶酸菜,可炒、可煮,败火消炎。当地人津津乐道的不只是菜,还有它的故事和诗文。
如果腌酸菜是过冬贮菜的古老真功夫,酱菜则已发展到专门制菜的大学问。山西做酱历史悠久,太原府酱、曲沃面酱、襄垣黑酱曾负盛名,为酱菜发展提供了基础。像大同红丝菜,原名“什香菜”,是老字号“庆和泉”酱坊的传统产品。每年秋天,该店将优质苤蓝去皮洗净,对角切成四块,一层苤蓝撒一层盐,码在池中腌制,6个月后取出切丝脱盐,入甜面酱中酱制15天,再将白酒、黄酒、鲜姜末倒入拌均,即成色亮、脆嫩、咸甜、醇香的佐餐小菜。
山西酱菜还有晋中的搅醋丝,相传源于明代,制法是白萝卜洗净,切成筷粗条状,置太阳下晒脱水分,再上笼蒸后晾凉,加酱油、醋搅拌,放在缸里密封半年。搅醋丝,色呈酱红、味含酸甜,口感软中带筋,配一碗细长的面条,既助食欲,又助消化。山西腌菜中名气最大的要数晋南临猗的酱玉瓜,1915年在巴拿马博览会上曾获金奖。这种以玉瓜和面酱为原料,经过半年腌制而成的酱菜,清脆爽口,曾畅销国内外,还远销日本和东南亚。但当四川榨菜跻身于世界三大腌菜之列,酱玉瓜却于市场踪声难觅,着实为山西人的一件憾事。即便像六必居、万新合这样的酱菜晋商老店,也扎根于北京、潼关,绽放它金字招牌的不落光辉。
红尘难掩晋俗风韵,洗去历史铅华的山西腌菜在返朴归真的文化潮中,正当崛起。想那文天祥后人文剑峰在英国开中餐馆,以一碟中国腌菜结识富孀而继承千万资产,是数十年“腌菜为媒”的敬老情谊。可见腌菜正如那“在水一方”的“伊人”,对老一代充满一份依恋的情怀,对新一代诉诸一份简洁的时尚,对事业未竟者是一份范仲淹“断齑划粥”、曹雪芹“冬噎酸齑”的励志。
若是烹字章章氽,必有腌文历历陈。诚如吾辈者当从宋代朱敦儒的 《朝中措》中品味一份腌菜的真谛:“先生馋病老难医。赤米餍晨炊。自种畦中白菜,腌成饔里黄薤。肥葱细点,香油慢焰,汤饼如丝。早晚一杯无害,神仙九转休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