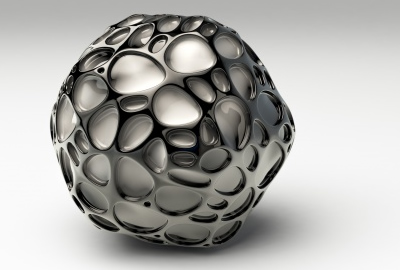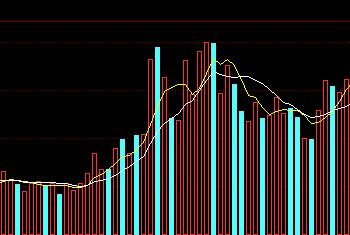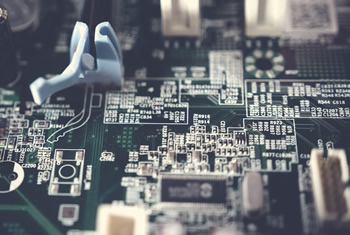登泰山记和赤壁赋的不同

《前赤壁赋》特点是“以文为赋”,《登泰山记》是“桐城散文”,初看似乎相似点很少,但仔细研读,这两篇文章其实可在主题的互补整合上做文章。
两篇文章均写于作者的失意之时。但同样面对不公平命运,苏轼与姚鼐的选择却又有很大区别。
先看泛舟赤壁的苏轼:
他先把自己的皮囊假托成一个悲情的”客“,这个“客”一悲英雄永逝(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二悲个体渺小(寄浮游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三悲人生短暂(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四悲壮志难酬(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悲从中来,不可断绝。这源于他儒家的事功思想。随后,苏轼心中的道家思想又以“主”的身份来宽慰儒家的悲怆,这个“主”分别以水月为喻,讨论了如何从变与不变两方面辨证地看待自然与自身。逝者如斯,江水奔流到海不复还,人不能连接两次踏入同一条河中,这是变;江水滔滔不绝,亘古如斯,这是不变。“月有阴晴圆缺”是变,“江月年年只相似”是不变。如果从事物变化的角度看,天地的存在不过是转瞬之间;如果从不变的角度看,则事物和人类都是无穷尽的。不要慨叹人生苦短,生不逢时,物我同一,生死同一,人生的意义可以永恒。于是乎苏轼的精神主体与世间躯体就“相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了。苏轼的解脱方法实是佛道圆融,从一定角度看也是一种自我麻痹——对于封建君权下的士人来说,这种圆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因为另起炉太劳累,在这种圆融中可以明哲保身,熬到下一次被皇家启用。
再看登泰山的姚鼐:
“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他不怕路途艰辛;“古时登山,循东谷入”,但他“道少半,越中岭,复循西谷,遂至其巅”,他不怕走“异路”;正因为如此,他看到了“苍山负雪,明烛天南”的夕阳壮丽,看到了“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的朝日磅礴。登泰山的历程其实就是姚鼐面对不公正人生的选择历程的写照,他不走常人之路,不怕另起炉灶,敢于舍弃已有的“坛坛罐罐”。
用个形象的比喻:
如果说苏轼和姚鼐面对的现实都是一个大黑球,苏轼能从这黑中看到一丝自慰的光明,并把它扩大,知黑守白,黑白交融,形成一个太极球;这个太极球向前滚动,可以走很远很远,但人终究只能在这个球中生存,变化。空间有限,改变亦有限。而姚鼐虽受的打压相对温和,但他的解脱之法却异常决绝,他没有滚太极,而是把这个大黑球捅破,他选择的是对旧有选择的放弃,另寻了一片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