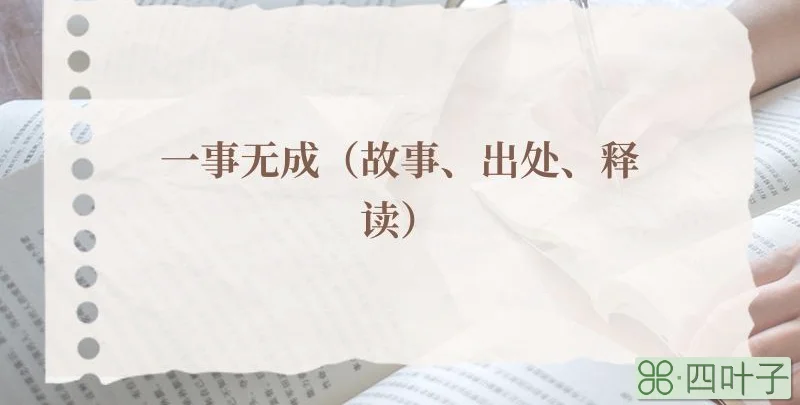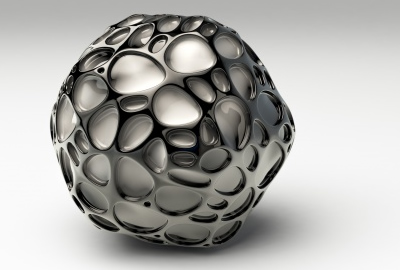我在天堂等你观后感

读完《我在天堂等你》,关于信仰和理想这个命题,引发我思考的不是两代人之间存在何种冲突、谁对谁错、哪个时代的信仰和理想更高级等问题,而是无论哪代人,在当时语境下应该怎样形成属于自己的信仰,并以切身的历练不断巩固之,在任何时候都不轻言放弃,自觉依靠信仰来消解对立面。
我想,任何信仰的形成都是一个艰辛的角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坚持一开始并不明了甚至飘忽不定的想法、信念,要放弃很多与信仰相背的东西,但也正是在这个坚持和放弃的角力中,信仰的质感和能量才逐渐显示出来.
信仰和理想始终与具体语境相关联,既产生于特定的时代,又和时代保持一定的距离;既镌刻时代的烙痕,也保有个体的意志;信仰和理想也是多层级多层次的自我系统。即使以书中白雪梅、欧战军等老一辈投身入藏革命、建设的群体来说,他们的信仰也并非仅仅产生于那个时代特有的单纯和激情,更不单单只是捍卫西藏领土、解放藏区群众、立志西藏建设的热情。热情是容易消散的,坚固的是热情褪去后的理性、责任、理想、抱负、信念,是他们在入藏跋涉中与战友用生命锻造的亲情、友情、爱情,是他们在艰苦历程中承受各种苦难后达到的心灵的安宁,是他们在大自然面前感受的敬畏和人类与大自然的融合,也是他们个体理想与群体信念乃至国家观念冲突后达成的和谐统一体。
书中有句话,“所有生活上的苦都不能算苦,所有生活上的难都不能算难,惟有心灵上的苦难才是真正的苦难。”那个时代的群体经受的苦和难,是物质富饶的和平时代的我们无法想象和体验的,然而与那些我们无法体验的苦难相比,他们依然认为心灵上的苦难才是真正的苦难,我想,信仰是通过承受心灵上的苦难而最终得以形成的,这是那个时代的群体/作者传达给我们的一种见解。我们无需争辩什么样的苦难才是真正的苦难,我也不认为生长在今天的我们承受的生活压力并非苦难的一种,只是,在我们承受生活上的种种苦难的时候,是否应该思考我们为什么而活,是成为苦难的奴隶,还是苦难的主人;是否应该思考我们在什么样的时代下生活,应该保有怎样的生活态度,是通过自己的生活、工作为自己的人生和所处的时代添上一笔光彩,还是一辈子无所坚持淹没于人海;是否应该思考怎样从生活的琐碎中提炼出超越生活的信念,坚持并保有一种独立的意志,放弃和拒绝环绕信念和意志的种种诱惑和同化…… 苦难是无法拒绝的,却也成就了一个人的人生。我想,人生的厚度有赖承受的苦难,并不在享受快乐的多少。
“有些人的生命是以应该的方式存在,有些人的生命却是以必须的方式存在。” 最后,引作者的一句话作结,这也说出了我的心声:“无论时代怎样变迁,社会怎样发展,我都敬重那些有着坚定信仰,并为之付出毕生努力的人,敬重那些始终如一为理想而奋斗的人,敬重那些重情义重责任重生命质量的人,敬重那些以生命为旗、灵魂为足而终生行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