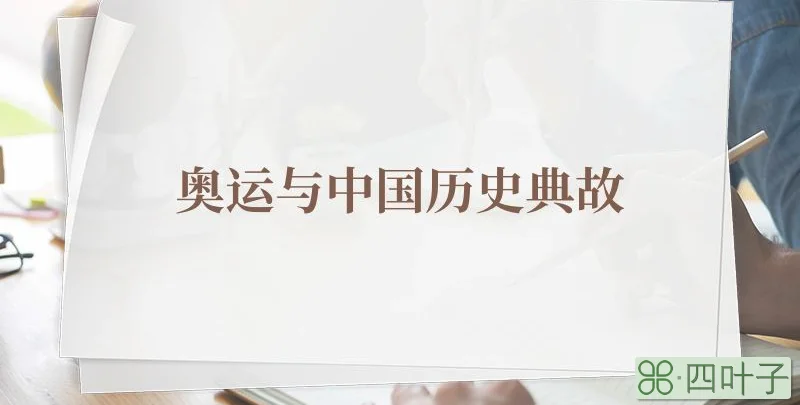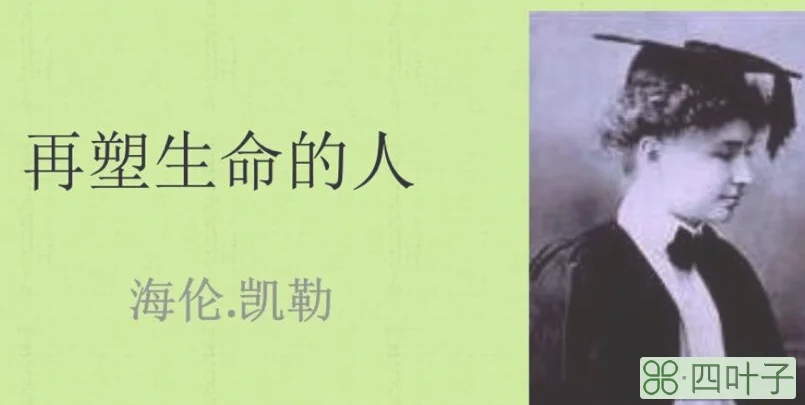哦香雪女性意识

在20世纪80年代“启蒙主义”的解读中,香雪透过“铅笔盒”对一个“现代化”的“明天”的渴慕正是她的超凡脱俗处。而近年来一系列“重返”与“重读”80年代的批评文章,均着眼于“新启蒙”解读对凤娇们的欲望的“遗忘”与“压抑”。罗岗、刘丽指出,凤娇们对“金圈圈”“手表”的欲望作为纯粹的“物欲”,相对于具有“象征性”“光环”的对“铅笔盒”的欲望,明显处于次等地位。正是“新启蒙”对“物欲”的“压抑”与“遗忘”,使它无法预见也无法应对在“物欲”驱使下进城务工的“凤娇们”将要面对的“直达她们的身体和内心的经济和超经济的剥削”,也无视了香雪对“铅笔盒”可能同样具有“物欲”的情感与态度。在程光炜看来,对“铅笔盒”的“明天”“善良”“纯真”“美好”等“精神意义”的超拔与提炼,内里是一种“知识分子主体意识”,它置换并压制了香雪对城市/乡村的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学”意识——一种“劳动人民主体意识”。而王钦的解读可视为对香雪/凤娇的欲望的等级关系的颠覆与翻转。在他看来,香雪对“铅笔盒”的欲望,背后是对“城市与乡村的空间差异时间化”、一套“经济发展的理性规划”的默认与接受;而在凤娇们的“物欲”中,“物质对象没有任何指向确定性未来、指向理想世界的附加值”,她们反而可能对城市与乡村生活作出自己的衡量,可能通过“火车停靠”和“物物交换”打开的“既不属于传统共同体,也不属于资本攫取的‘人力资源市场的时间/空间”,进入有别于“作为劳动力资源的经济个体”的另一种“个体化进程”。
单从1980年代“精神性”与“物质性”的等级关系出发,无法解释小说为何让持有“精神追求”的香雪对抱持“物欲”的凤娇怀有如此强烈的亲近与依恋——当凤娇在姑娘们的揶揄中受了委屈,香雪“悄悄把手送到凤娇手心里”,“她示意凤娇握住她的手,仿佛请求凤娇的宽恕,仿佛是她使凤娇受了委屈”;也无法解释小说为何执意以“闲笔”表现,香雪对“铅笔盒”也可能具有凤娇们对“金圈圈”“手表”同质的感情——当她终于得闲品味对“铅笔盒”的占有,首先往里面装进了“盛擦脸油的小盒”,“只有这时,她才觉得这铅笔盒真属于她了”。小说中,“铅笔盒”与“金圈圈”“手表”作为欲望物的等级关系是确乎存在的,但要剖析这种等级关系,剥除前者的“象征性光环”仅是其中一步,审察后者的“物质性”是同等必需的。即便同作为“物质”“本身”,“金圈圈”“手表”相对于“铅笔盒”仍有自身的特异性——它们是对“女性外表”的装饰物。于是,对“金圈圈”“手表”的欲望受到压抑,也许并非是——至少并非仅是因为它们是一种“纯粹”的“物欲”,而是因为它们是一种“特殊”的“物欲”、一种“女性化”的“物欲”。
然而,关于“女性外表”的欲求为何受到压抑,这同样需要获得解释。在1980年代的语境里,它同样可能被表述为女性“天性”的需求,是“自然”而“正当”的。我们只能继续从上下文寻求理解。小说中,与“金圈圈”及“手表”并存的、乡村少女们的另一个话题热点,是火车上的乘务员“北京话”。这个“白白净净”“身材高大、头发乌黑,说一口漂亮的北京话”的年轻男乘务员是少女们相互打趣调笑的对象。与凤娇在“金圈圈”话题里的领头者身份相仿,她也是这类调笑的主要对象。而当凤娇试图反唇相讥,姑娘们便说,“我们不配!”这种调笑便很接近于一种“推举”了。尤其是在和火车上的人做买卖时,“凤娇好像是大家有意分配给那个‘北京话的”。而凤娇虽然在面对姑娘们时“嘴很硬”,但还是相当乐意与“北京话”做买卖,并且刻意要做成不等价的、延时的、非“一般”的买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