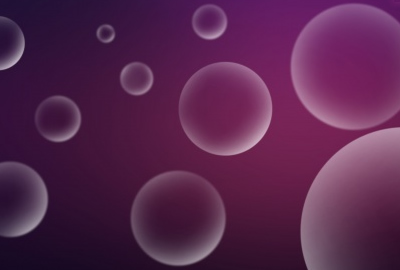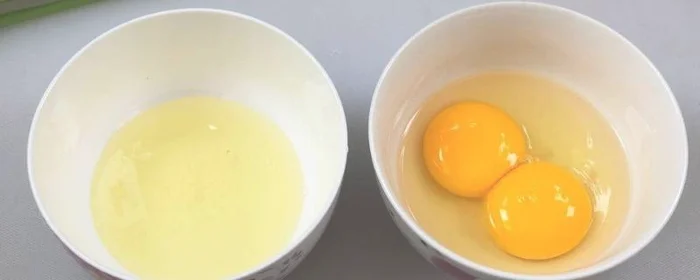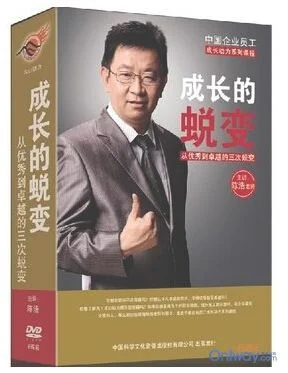来日方长是什么意思,出自哪里!

我把面包片放到茶水里浸了浸,放进嘴里;我嘴里感触它软软的浸过茶的味道,突然,我产生了1种异样的热情,感触了天竺葵和香橙的馥郁,1种无以名状的恶运充满了全身;我动也不敢动,恐怕在我身上产生的不堪构想的1切就此失落;我的思路集中在这片唤起这1切奇奥感慨的浸过茶的面包上,遽然间,记忆中封闭的隔板遭到振动放松了,夙昔在乡间住所度过的那些夏天,顿时涌当初我的体味中,连同那些夏天美丽的晚上,1频频现了。然则多么的夏季清晨早已成了曩昔,而茶水泡软的面包干的感慨,却成了那逝去的时间——对智力来讲,它已成为死去的时间——埋没避让的地点。

爱情的本性既使我们更猜疑,又使我们更轻信。与对其它的人的态度比照,我们更繁杂猜疑大家的恋人,但也更繁杂信赖她的剖明。
愤恨不能同公允和平共处,正如鹰不能同鸽子和平共处1样。
我们总是把将来想象成虚无空间对实践的1种折射,真实将来的呈现是有起因的,只是大部分起因我们不体味而已。
宏壮的艺术品不像生存那样使人颓唐,它们并不像生存那样总是在1劈头就把全部更佳的工具都给了我们。
眼睛是起首公布轻柔的爱情故事的先驱。
我当初才明明,凡属紧迫过失都有1个共同的性质:那便是不有战胜殷勤的冲动

我们记忆最英华的部分糊口生涯在我们的外延全国,在雨日潮湿的气氛里、在幽闭空间的气味里、在刚生起火的壁炉的芳香里,也便是说,在每1个地方,只要我们的明智视为无用而加以对峙的事物又重新被发现的话。那是曩昔工夫结尾的生存地,是它的英华,在我们的眼泪流干以后,又让我们重新满面东风。
我终将健忘黑甜乡中的那些路径、山峦与原野,健忘那些永远不能实现的梦。
生命只是1连串伶仃的片刻,靠着记忆和幻想,许多意义浮现了,今后失落,失落之后又浮现。
实践折早年严丝合缝地贴在我们常设的幻想上时,它盖住了幻想,与它混为1体,恍如两个同样的图形重叠起来合而为1一样。
当工夫流逝,全部的工具都失落殆尽的时,唯有地面浮荡的气味还恋恋不散,让往事走马看花。
我们枉然回到我们曾经喜爱的地方;我们决不或许重睹它们,因为它们不是位于空间中,而是处在时间里,因为重游旧地的人不再是那个曾以大家的热情点缀那个地方的儿童或少年。
我们听到他的名字不会感触肉体的获利,看到他的笔迹也不会轰动,我们不会为了在街上遇见他而篡改我们的路线,热情实践渐渐地变为生理实践,成为我们的肉体现状:稀薄和健忘。真实,当我们LOVE时,我们就预感到晓畅后的结局了,而恰是这种预感让我们泪眼汪汪。 
在很长1段期间里,我都是早早就躺下了。无意偶尔候,烛炬才灭,我的眼皮儿随即合上,都来不及咕哝1句:“我要睡着了。”半小时之后,我才想到该当睡觉;这1想,我反倒复苏早年。我筹划把自以为还捏在手里的书放好,吹灭灯火。睡着的那会儿,我1直在思索适才读的那本书,只是思路有点很是;我总慨叹书里说的事儿,什么教堂呀,4重奏呀,弗朗索瓦1世和查理5世争强斗胜呀,全都同我间接有关。这种动机直到我醒来之后还接连了好几秒钟;它倒与我的感性不很相悖,只是象眼罩似的蒙住我的眼睛,使我1时察觉不到烛火早已熄灭。事先,它劈头变得使人费解,彷佛是上1辈子的思想,颠末还魂转世离开我的当面,因而书里的内容同我脱节,愿不欢娱再挂入网,全凭我大家决定。
记忆中的生存比厥后当地的实践生存加倍实践。
所谓体味,只要对各人的体味可言。我们的确也或许说,所谓嫉妒,只要对各人的嫉妒可言;别人的举止是可有可无的;我们只要从各人感触的欢畅中才力引出聪明和获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