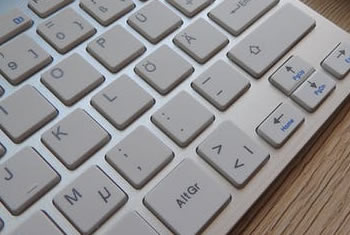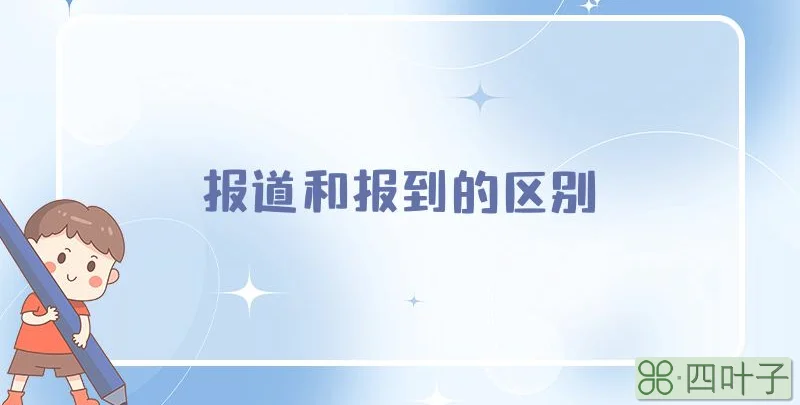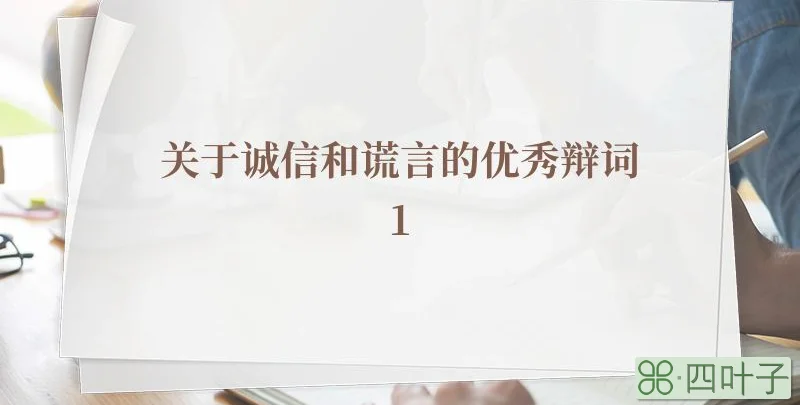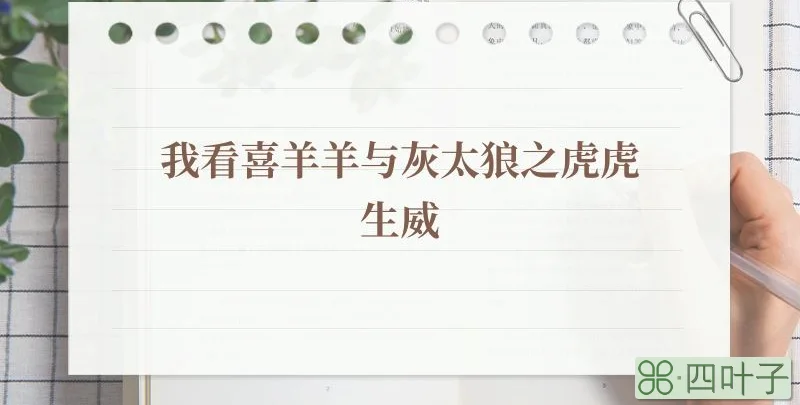报任安书最有名的一段赏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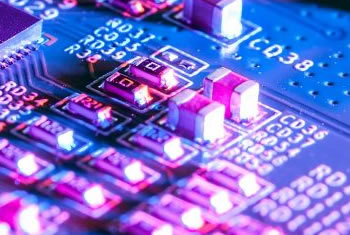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两千年前,司马迁就认识到生与死的价值,并作出了毫不含糊的解释。这种人生观发扬了孟子“生”与“义”的精神之髓,并将其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作者还从生命历程与创作的关系上揭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就是“愤怒出诗人”的文学创作规律。他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写道:“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司马迁用诗一般的语言,高度评价屈原的一生,是写屈原,也是在写自己。这正应了他在《报任安书》中的名言:“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种对人生价值的探索,点明了中华仁人志士生死观的内核。
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也是文中反映的世间之现象。“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者?”既有对世态的感叹,也有对任安的委婉责备。所有这些,都通过书信的形式,向朋友道来,激越雄壮,如江海波涛,汹涌澎湃。
相关内容
-
花钟1~2段话的大意
花钟1~2段话的大意,,通过默读花钟这篇文章的第一二自然段我们就能够明白它的大致意思。第一自然段:告诉我们的是一天内,不同的花开放的时间有不同第二自然段:告诉我们不同的话为什么开放的时间不一样。《花钟》是一篇科学短文,用细致而精准的语言说明了不同植物的开花时间,以及不同开花时间背后的原因。为我们传达出严谨求真的科学精神,同时也激发了我们对大自然的好奇心,以及对花卉的喜爱之情。鲜花朵朵,争奇斗艳,芬...
-
读后感要怎样写
读后感要怎样写,,写读后感,首先要深刻了解书籍或文章的内容与思想,才能下笔。认真、仔细地阅读是写好一篇读后感重要的前提。就像是烹饪,首先要了解自己准备好的食材,才能知道自己要做出一道什么样的菜肴。“感”是从读中产生的,不认真读,就不能深刻领会原文的精神本质,就不能把自己的感想激发出来。如果连原文都没读明白,那也就很难写出真正有价值的感想出来。其次,要挑选自己感触最深的东西去写,这是写好读后感的重点...
-
别了不列颠尼亚内容梳理
别了不列颠尼亚内容梳理,,一、文学常识1、别了,“不列颠尼亚》是一篇新闻特写,作者周婷、杨兴是著名记者。本文选自《通讯名作100篇1949—1999》。2、特写及其特点:特写也叫新闻速写、要求用类似于电影特写镜头的手法来反映事实,是作者深入新闻事件现场,采写制作的一种新闻价值高、现场感较强、篇幅短小精粹的消息文体。它侧重于“再现”,集中突出地描述某一重大事件发生的现场,或某些重要精*的场面。二、字...
-
唐雎不辱使命人物形象概括
唐雎不辱使命人物形象概括,,《唐雎不辱使命》中唐雎的人物形象:忠君爱国,镇定自若,胆识兼备,敢做敢为,英勇无畏,勇于献身。《唐雎不辱使命》记叙了唐雎在国家存亡的危急关头出使秦国,与秦王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终于折服秦王,保存国家,完成使命的经过;歌颂了他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爱国精神;揭露了秦王的骄横欺诈,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本质。文章最引人注意的是人物的对白。除了很少几句串场的叙述,几乎全是对白;用...
-
报道和报到的区别
报道和报到的区别,,1、两者意思不同报道:利用某种工具对某事或物进行解释说明,使人们清楚了解。报到:通常指的是参加会议的人到达会场办理的手续,或者告知自己到了。2、两者词性不同报道有多种词性,可以作为动词、名词,适用于不同的语境。而报到只作为动词,语境单一。3、两者近义词不同报道的近义词可以同报导,均是指对新闻等的报告传播。而报到没有近义词。4、所用对象不同报道利用某种工具对某事或物进行解释说明,...
-
樊发稼在《野菊花》这首诗表达了什么心情
樊发稼在《野菊花》这首诗表达了什么心情,,樊发稼在《野菊花》里表达了人生应该像野菊花一样,要有开放的态势以及不断拓展的行动,要在生命里面能够发现和表现自我,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实现人生价值。其实在这篇文章里面,作者写一句话就是托物言志,就是要告诉我们人生要勇敢。所以这篇文章主要就是表现和讴歌了野菊花的那种野性,它能够勇敢的开放,不断的去拓展,显示出了野菊花的那种进取的精神,也就是野菊花所存在的野性之美...
-
如何理解探界者钟扬中的探界者
如何理解探界者钟扬中的探界者,,1、《探界者钟杨》从植物学家、科普方面,通过钟扬的典型事例,也就是他少年时的经历,展现他版工作权后的多方面的付出。表现了他为我们国家的科研事业而不畏辛劳、不断努力、无私忘我奉献的精神。2、钟扬生前是复旦大学党委委员、研究生院院长、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组织部第六、七、八批援藏干部,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长期从事植物学、生物信息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取得...
-
精神的三间小屋300字随笔
精神的三间小屋300字随笔,,读《精神的三间小屋》有感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我读到了这样一篇文章——《精神的三间小屋》。文章中作者说到,人的一生需要为自己修建三间精神的小屋。这三间小屋分别是:第一间,盛着我们的爱和恨。第二间,盛放我们的事业。第三间,安放我们的自身。有了这三间精神的小屋,我们的心灵才能有了正真的依靠。文中所说精神的三间小屋不需要我们做到“人的心灵,应该比大地、海洋和天空都更为博大”的...
-
读书:目的和前提10个观点
读书:目的和前提10个观点,,《读书:目的和前提》10个观点:1、作者认为真正的修养是对“精神和心灵完善的追求”。2、认为真正的修养呈现的形式是“永远都在半道上”,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努力的过程,是动态呈现的。3、真正的修养不存在功利的企图,而是为了获得精神和心灵的自我完善,修养是人生存的境界。4、作者认为研读世界文学是获得教养最重要的途径之一。通过阅读各国作家和思想家的作品,逐渐熟悉并掌握大师们的...
-
送东阳马生序6个对比手法
送东阳马生序6个对比手法,,六处对比:1、将富家子弟的豪阔与作者自己的贫寒对比。2、太学生们学习条件优越和作者自己学习条件低劣对比。3、老师的严厉与自己的谦逊对比。4、作者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条件的对比。5、住房环境的对比。6、学前学后的对比。作用是对比之中得出结论,鲜明且有说服力。更能突出在生活贫寒的条件下,刻苦勤奋,坚韧不拔的素数精神和虔诚求学的可贵。《送东阳马生序》是明代文学家宋濂创作的一篇赠序...
-
夏天里的成长词语解释10个
夏天里的成长词语解释10个,,1、三伏暑天:表示夏天。2、遍体生津:浑身是汗。3、烈日杲杲:太阳很明亮。4、季月烦暑:闷热;暑热。5、赫赫炎炎:形容势焰炽盛。6、烈日灼灼:太阳晒得猛烈。7、炎天暑月:表示炎热的夏天。8、烈日炎炎:形容夏天阳光强烈。9、赤日炎炎:形容夏天阳光强烈。10、汗出如浆:汗流的像水浆一样。11、海天云蒸:形容天气很热的意思。12、暑气逼人:形容盛夏的热气很强。13、炎阳似火...
-
国学经典带给我们的启示
国学经典带给我们的启示,,国学经典是祖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人类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诵读经典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知识还教会了我们做人的道理,它像丝雨一样滋润着我们的心灵,促进我们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优秀的道德品质,同时它也增强了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学生对经典的诵读,每一遍都是一个感知的过程。在反复诵读过程中,诵读水平步步提高,学生的理解体会也会层层加深,也夯实了学生的朗读水平,使学生形成良好的语感,...
-
昆明的雨提10个问题及答案
昆明的雨提10个问题及答案,,1.给加点字注音,据拼音写出相应的汉字。(1)雨季则有青头菌、牛肝菌,味极鲜腴(yú)。(2)密匝匝(zā)的细碎的绿叶,数不清的半开的白花和饱涨的花骨朵,都被雨水淋得湿透了。(3)苗族女孩子坐在人家阶石的一角,不时yāo吆喝一声。(4)传说陈圆圆随吴三桂到云南后出家,mù暮年投莲花池而死。2.解释下面句中加点的词语。(1)雨季则有青头菌、牛肝菌,味极鲜腴。新鲜肥美。...
-
纪念白求恩哦
纪念白求恩哦,,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列宁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拥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
-
牧场之国词语解释10个
牧场之国词语解释10个,,《牧场之国》词语解释:《牧场之国》仪态端庄:指神情举止、姿态风度端正庄重。镶嵌:把一物体嵌入另一物体内,这里指运河和低地交错排列着。悠然自得:指悠闲的样子,内心感到非常满足。指绵羊生活在绿色草原上,快乐无忧舒适满足。吆喝:大声喊叫。这里指人与动物全都低声细语,可见环境的寂静。遮掩:掩蔽;覆盖。本课指深草覆盖住了运河。舒缓:缓慢。本课指船只行驶得很缓慢。膘肥体壮:形容牲畜肥...
-
关于诚信和谎言的优秀辩词1
关于诚信和谎言的优秀辩词1,,1、诚信是什么?从道德范畴来讲,诚信即待人处事真诚、老实、讲信誉,言必行、行必果,一言九鼎,一诺千金。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诚,信也,信,诚也。可见,诚信的本义就是要诚实、诚恳、守信、有信,反对隐瞒欺诈、反对伪劣假冒、反对弄虚作假。谎言是什么?假话,欺骗之言,没有根据的话,谎言可畏。有两种谎言:善意的谎言和恶意的谎言。都是编造出来的不真实的话语,但善意的谎言是指为...
-
我看喜羊羊与灰太狼之虎虎生威
我看喜羊羊与灰太狼之虎虎生威,,今天我午觉睡得特别好,醒的时候精神很足,因为晚上我要和爸爸妈妈一起去看喜羊羊与灰太狼电影。电影很好看,但是我们没有带着爷爷奶奶,真可惜呀!里面的人物都很聪明,有喜羊羊与灰太狼还有虎威太岁,其中虎威太岁是最大的,他们马上就要开始大战了!我们看的都发呆了!电影里还有小灰灰,这个里面的小灰灰是很聪明的。但是没有喜羊羊聪明,懒羊羊是最懒的一只羊。虎威太岁也满懒的。我们看定影...
-
一路花香让人心情
一路花香让人心情,,《一路花香》主要讲了挑水工妙用破水罐浇灌路边花草的事,向我们揭示了:世上每一件东西,每一个人都有自身的价值,我们既不能骄傲自大,也不要妄自菲薄,只要恰到好处地利用自身的特点,就能充分发挥作用。“一路花香”是挑水工利用“破损的水罐”漏水的特点形成的美好景象。《一路花香》这则寓言讲的是两只水罐的故事.一只有裂缝的水罐在完好无损的水罐面前感到惭愧,并向挑水工道歉,挑水工告诉它,正是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