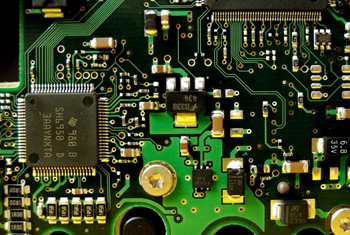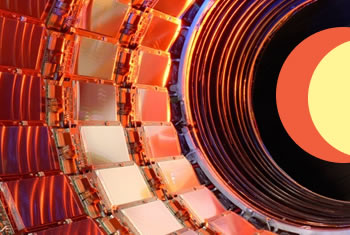精读和略读哪个更重要辩论

精读和略读哪个更重要
精读与略读历来是学问家读书的焦孟之法,从来没有哪个人一生只靠博览群书而最终学有所成的,更没有哪位大哲先贤平生只读一本书而成名成家的。晋人陶渊明自述好读书不求甚解,可谓博览群书的典范,可是任谁都能想到他也曾有过学有专攻的少年时代;宋人赵普曾自谦说自己是半部论语治天下,可是一千年来没有哪个呆子真会相信他一辈子只读过论语,而且还是半部。
略读带来高效率,它能在较短时间内帮助我们汲取大量信息,很适合快节奏的现代社会。西方发达国家大都注意学生略读速读能力的培养,因而他们的孩子思维灵活、视野开阔、知识面丰富,这一现象已经引起我国教育界的注意和重视,如何提高学生略读能力和阅读量日渐成为教育工作者尤其是一线教师关注和探讨的问题。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相信不久的将来,我国儿童的阅读状况一定会得到整体改观。而与此同时,精读却由于费时费力,越来越为人们所不取,这其实是一件很不明智的做法。因为无数学问家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精读的作用不可替代。它不但能在最大限度上最全面地吸收书本所蕴含的信息,而且能起到锻炼思维、引人深思、启发智慧的作用,所得远甚于走马观花的略读。
目前无论家长还是老师,甚或整个社会,大都以提高学生阅读量为己任,老师教研或家长聚会听到的大都是最近孩子有读了几本小说、看了几本童话,数目越多便显得成绩越大。这本没有错,家长老师社会重视阅读是件好事,我在《可怕的差距》一文中也曾针对加拿大小学生年平均阅读量过千万字的现状发出提高我国学生阅读能力和阅读量的呼吁。然而如果片面注重略读而忽视了精读,那么就丢掉了我国源远流长的优秀读书传统,不利于学生对知识的深入领悟和研究,更不利于学生。宋朝大诗人苏东坡就是精读的高手和忠实实践者。
一天,有位朋友去看苏东坡,发现他正在抄《汉书》。朋友感到很不理解。凭苏轼的天赋和“过目成诵”的才能,还用得着抄书吗?苏轼说:“我读《汉书》到现在已经抄上3遍了。第一遍每段抄3个字,第二遍每段抄两个字,现在只要抄一个字了。”客人疑信参半地挑了几个字一试,苏轼果然应声能背出有关段落,一字不差。苏轼不仅三抄《汉书》,其它如《史记》等几部数十万字的巨著,他也都是这样一遍又一遍地抄写的。苏轼称它为“迁钝之法”。然而正是这迁钝之法成就了一代大家。苏东坡的抄书其实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精读。现代著名散文家秦牧主张读书要学会“牛嚼”和“鲸吞”。鲸吞当然无异指大量的略读,牛嚼自然是精读了。他说:“老牛白日吃草之后,到深夜十一二点,还动着嘴巴,把白天吞咽下去的东西再次“反鱼’,嚼烂嚼细。我们对需要精读的东西,也应该这样反复多次,嚼得极细再吞下。有的书,刚开始先大体吞下去,然后分段细细研读体味。这样,再难消化的东西也容易消化了。”由此可见,略读精读的确哪个也偏废不得,只有二者结合使用才是真正的读书良法。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我在引导学生开展课外阅读的同时,不但鼓励他们博览群书、广吸海纳,号召他们每人每年至少250万字的阅读量,更注重知道他们进行有目的有选择的精读,试验两年来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现在将操作方法做一简单总结。
我一直主张每个学生甚至每个老师都要做到一年精读一本书。通过精读一本书,不但可以学到语法修辞、写作方法,还能训练语感、积累语言,甚至能起到端正思想、优化思维、安身立命的巨大作用。一本书成就一番事业、一本书改变一个人的故事绝非天方夜谭。
既然精读的意义这么深远,既然一年只读一本书,那么挑选什么书作为精读对象就显得至关重要。教学中我一般采用教师引领在前、学生自由选择的办法,指导学生精心挑选所读数目,总的原则是首选古今中外各类名著,难度略高于学生水平,写作风格以明白晓畅为佳,如《上下五千年》、《二十五史故事》、《郑渊洁系列童话》、《爱的教育》、《鲁滨逊漂流记》、《杨红缨系列小说》、《红楼梦》等都是学生喜爱的好书。
提到精读难道就是读得慢一点,一个字一个字崩吗?当然不是的。我说过,我们的做法是一年精读一本书,因此无论读书的时间安排还是读的具体方法我们都有特别的讲究,绝非抗日持久的磨洋工。具体说来说,我们一般将整个读书过程分作六步,下面分别加以介绍。
第一步,快速浏览。
第二步,逐句精读。
第三步,放声朗读。
第四步,全书抄写。
第五步,精彩段落背诵。
第六步,升华提高。
事实证明,在鼓励学生广泛略读的同时,激励学生进行有步骤有目的的精读,对学生语感、思维、口头表达、学习习惯、生活态度、性格气质等各方面的影响是深刻和深远的,只要教师认真引导、步步抓实,其效果非泛泛而读所能比拟。